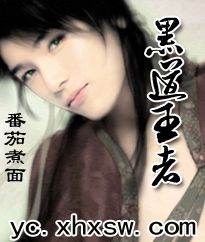正文 -- 二十五集好事多磨挑佳婿
二十五集好事多磨挑佳婿
说书人: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是皇家宫庭轶事艳闻,更是茶舍酒楼消闲遣闷助人兴趣的话题。皇家禁卫龙武军,青天白日拦窃有着东宫标志的四马轿车,倾刻风雨满京师也传入了紫禁城。太子李弘心怀叵测武后已有觉查,为防不轨,这窃轿之事,是否是蛛丝马迹,她岂能放过。
沛王府中,花园草坪上太平公主和宫女嬉嬉放风筝。庭院内李贤与李显正在斗蟋蟀,他们的侍从们也和二王子混杂围观,众人都被两个小虫的拼咬撕杀,牵引得惊呼呐喊。一只小虫被惊,跳出了斗争的精致瓦罐。
李显拍手欢呼:“啊!我的红头大将军胜了!”
李贤不不服:“不算不算,我的紫玉元帅是被你大吼吓得跳出斗钵的!”
李显:“你输了!”
李贤:“我没输!”
“没有决出胜负,你们再斗嘛!”武后已进到庭院中。上官婉儿和随从宫女太监也侍立一侧。
李贤李显急忙跪迎:“母后千岁千千岁!”
王子的侍从也全都跪拜:“娘娘千岁千千岁!
武后微笑道:“你们兄弟俩谁斗得过谁呀?”武后以手示意下,二王子与侍从都立起了。
李显亲切地过去:“母后,我和二哥在斗蟋蟀。”
武后意味深长地说:“蟋蟀虽小虫,天性爱争斗,同类拼杀毫不留情。一个任命为将军,一个被封为元帅,你兄弟操纵它两争胜负;力大为王,不是斗虫是斗气吧!”
李贤辩护道:“我们兄弟和睦,亲如手足,斗蟋蟀博彩,哪能因物及人,去斗什么气。”
武后叹道:“父母兄弟骨肉亲情,千万不要再像当年斗鸡,逼着王勃写那挑战的斗鸡檄文,让你们父王,误认为是他挑拨你们兄弟不和而争斗。将个有心报效朝廷的贤能,贬到剑阁去遭磨难。”
李贤道:“母后不是为他金盆雪冤,已经召回京来了么。”
武后:“树怕伤皮,皮伤留有疤痕在;人怕伤心,心伤难以消积怨。”
李显大咧咧地:“母后一次次对他施恩,他知恩不报,就是不忠。这不忠的臣子,留有何用,儿臣去将他斩了!”
武后笑了:“你这算是什么道理,好马不吃回头草,不能因为它不吃回头草,是好马你也斩了它。你不斩,还正有人想借你刀,斩了你的好坐骑呢”。
李显不服:“哪能有这样的事?”
李贤聪明了一点:“有,不是有人篡改诗稿,让母后断章取义去冤杀王勃吗?”
李显又替王勃抱不平了:“这人是谁,我替王勃去斩了他!”
“斩斩斩,”武后又笑了:“你那宰牛刀,能敌得过上方宝剑吗?”
李显反而来劲了:“母后你将上方宝剑赐给儿臣,我替母后去斩了那奸贼佞臣。”
武后收敛了笑容:“得了,若依仗你们这些整日沉缅在声色犬马,斗鸡玩虫的龙子凤孙身上,李氏大唐的江山社稷,早已落入别有同心的功臣重将的名下了。”
李贤觉得逆耳:“母后是否危言耸听了!”
李显更不服气:“将门出虎子,我们是嫡嗣龙种,不是那黄鳝泥鳅!”
武后走入内厅,转身说道:“为娘四个龙儿一个凤,就盼望你们不坐龙庭的,也都是能治国安邦的王侯公卿。可你们呢……唉,王权不能旁落。历朝历代总有那些逆臣奸佞。虎视眈眈盯者龙廷宝座,才有那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
李贤不解:“母后,你今日来此说这些为什么?
武后示意婉儿摈退他人后语重心长:“就为了李氏大唐的千秋大业,王权不能旁落,为娘望你们关注江山,执干戈捍卫社稷,能治国安邦者才能为帝王。”
李显初闻此言:“大哥李弘早已是父王册封了的储君东宫皇太子呀。”
武后平淡地说:“你们父王的兄长李承乾贪恋男宠无有后终被贬为庶人死于蛮荒西南;你们同父的兄长李忠册封为太子,愚昧无能难掌王权,也被父们父王贬为梁王,迁出东宫去安享富贵,他竟穿着女装混日子,扰得臭名远扬。古往今来册封为王储,居东宫不修身养性,不励图长进,不能安天下者,有几人承天命而登大宝,驾坐九龙御座的?”
李贤侧面相问:“难道我们兄长李弘他,他有失德的过犯?”
李显冒失直言:“我大哥他已不配当东宫太子吗?”
武后:“他是否罪已失德,他配不配继承王位。这是要你们兄弟观察,朝野群臣鉴别,天下百姓拥戴;而由真命天子当朝皇上,你们父王明断来降圣旨的。”
李贤:“父王宠爱李弘,早已有禅位的意图。”
武后:“此一时彼一时。至今圣上并未禅让了龙位。”
李显也动心了:“可是我大哥忠孝仁义的美名已是满朝赞誉,天下传扬了啊!”
武后明言不讳:“那是长孙无忌之流,和别有图谋的奸佞,还有那献媚邀宠的太史令们,迎合你们父王一时的蒙昧,替李弘这奴才涂脂抹粉,吹嘘宣扬的浮夸言论。虚张的声誉。”
李显直逼要害:“母后你认为李弘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吗?”
李贤聪明地反问:“李弘大哥,他真是那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假圣贤吗?”
武后一言定乾坤:“你们也是真命天子之子,你们也是当朝英明圣上之后。以你们自己修身立德之德,来鉴别你们这位兄长,他是否是位名实相符大唐王朝的继承人。这还用我来明说吗?”
二位太子张口难言,李贤狡黠地:“儿臣今后不再迷恋犬马,一定奋发图强,力求能像母后德智双全,一眼就能辩明是非。”
李显直言快语:“我早就看出来了,大哥是个阴一套阳一套,心术不正爱暗中捣鬼的人。”
武后明言已见:“你二人今后暗中要多多关注你们大哥的一举一动。”
李贤有所猜想:“莫非母后你……。”
“我们母子不能让你们兄长被奸佞迷惑误了江山社稷,丧失了他的锦绣前程。”武后目的达到就转了话题:“你们的妹妹太平呢?”
“母后,惹你心烦,气恼,讨厌的不能太平的太平鸟儿在这里呢?”太平公主从画屏后,一身玩乐时的紧身衣衫窜了出来。
武后笑着斥责:“瞧你这疯丫头,疯到哪里去了!”
太平偎到武后怀中撒娇地:“你让我邀了三哥到二哥府中等你。你呀又不知被什么国家大事缠住了手,裹住了脚,让我这小姑娘快等成老太婆了。”
“哪好,你这老太婆丑得没人要,免得为娘的要操心到老鼠洞里去给你找驸马!”武后逗女儿。
太平甩开武后娇嗔地:“母后,我的驸马我自己挑,用不着月下老人牵红绳,父母下军令。”
武后笑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满天下都是无媒不成亲。那有个黄花闺女自己挑男人的。”
“有!”公言大言不惭地宣布:“我不仅自己的驸马自己挑,也要为抱怨是:‘断线风筝女儿命’的大闺女抱打这不平!”说罢从随身宫女手中拿过了一个大花蝴蝶风筝。
“风筝?”武后被精美的风筝吸住了。
李贤道:“妹妹不爱斗蟋蟀,就带着些宫女们到后花园放风筝了。”
“就是她爱出奇招。春天熏风上扬才放风筝,求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太平公主分辩:“秋天金风送爽照样能够放风筝,人家求的是情投意合,一改故辙,不求月老系红绳,自寻郎君自风流。”
武后训斥地:“你这丫头,不遵女训尽出格,这样的话闺阁少女怎么说得出口。”
公主笑道:“所以才敢秋高气爽,不按气节放风筝,你看!”太平将风筝塞到武后手里。
武后颇感兴趣:“扎得精巧精致,画得美妙美丽。”
“巧就巧在女儿的心意,妙就妙在借着风筝敢怨天。”
武后看风筝另一面:“哦,一首诗,好娟秀的字体。”她念诗文:“
唯愿秋风送春暖,
呵护彩蝶向云天。
断线风筝女儿命,
红绳何需任人牵。
“这是你的心意;可不是你手笔。这是谁替你题诗抒怀了?”
公主笑道:“我是敢想敢说敢为,她呀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扎个风筝题诗向着老天发牢骚。”
武后追问:“这风筝你是哪里得来的?”
公主:“‘断线的风筝女儿命’随风吹,她与我有缘,给我拾着了。”
“这诗的题款是阎氏秀芹,不知是谁家的才女。”
武后随从:“启奏娘娘,阎伯屿应召前来门外候旨。”
武后:“宣他进来吧!”
李贤疑问:“母后是特地召他来我府内竭见的吗?”
武后:“这是为了避免他人疑神疑鬼。”
阎伯屿进入厅内叩拜:“老臣叩见娘娘千岁千千岁。”
“起来吧!”武后向婉儿:“给老将军端把太师椅来。”
阎伯屿歉逊地说:“老将年过花甲,还没有老弱年迈。”
“坐下说话。”
“谢谢娘娘。”
武后笑道:“你是老骥伏枥心不老,精神着呢。可京都九门捍卫紫禁城,这可不是昔日你随先王太宗那个西征;血战黄沙敌我分明。现在朝野上下鱼龙混杂,有人想扰浑了水,兴风作浪图谋不轨,你这位能冲锋陷阵的老将军,能辨清忠奸,识破鬼魅的伎俩吗?”
阎伯屿好胜地说;“老臣也指挥过千军万马……”
“哀家知道你武功过人,只是文韬不足;又逞强好胜,不肯让人。老了就是老了。这里你若能答清哀家所问,我就让你继任九门提督。”
“皇后请问。”
“你那文武不济,擅长空谈的侄儿阎望远,为报效朝廷,也困死在东征的异国他乡。这么多年劳民伤财,号称大捷的战争,人之常情必有民怨。以你之心度他人,他们该怨谁?”她见阎伯屿不答,又问:“该怨太子李弘邀功好战?还是怨皇上昏庸纵子误国?还是该怨哀家不及早制止这不义之战?”
阎伯屿:“老臣纵有斗胆,岂敢怨天。”
武后笑了:“你不敢回答,也难回答,更答不清楚。”她见阎伯屿已无豪气,又问:“昨日你部下闹市中将太子东宫的轿车,劫持到纪王府,为了何故,这车中劫持的是何人?阎伯屿心虚了:“老臣是奉纪王爷之命而劫持了御用马车,并不知劫持何人?”他又急于分辩:“纪王乃是老将昔日主帅,他又是太子妃的老祖父。我命部下及时拦车押入纪王府,不知其中的内情。这,这这也是皇亲国戚的家务事,老臣奉命行事,不敢过问,那敢干涉。”
武后冷笑道:“哼哼,好个上命下达,清官难断家务事。”她一转话锋尖刻的说:“这车上若劫持的是哀家的忠臣义士。你这维系着皇城安危的九门提督。竟敢不分忠奸,不明事由,就为虎作伥,协助了叛乱,这可了得!”
阎伯屿吓得跪伏在地:“罪臣,罪该万死!”
武后哈哈大笑:“哈哈哈,你这奉命的劫持,不过是一场皇族家务事,东宫里太子小俩口子,小打小闹,不吵不闹就不热闹嘛!婉儿快将老将军扶到太师椅上。老将老将,原本是老虎,老了就成了老鼠。不服老不行啊!”
阎伯屿无可奈何:“老臣年迈,不中用了……”
“谁说你不中用了?”武后先打后优抚:“老马识途,不能冲锋陷阵就驮辎重,你还下不了疆场呢。”
阎伯屿直言粗语:“老臣自幼五大三粗,天生是个宁为鸡头不作牛后的犟牛,如今老了,娘娘留我当根牛尾掸苍蝇,还是……。”
“还是让你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养老说穿是安心等死。”武后一本正经的说:“我永不会服老,我要老当益壮的兴国安邦老有所为。你是开国有功,兴邦无过的两朝元老,是哀家耳濡目染少有的忠义勋臣,是哀家的股肱重臣。”
阎伯屿感恩载德老泪横流:“士能为知已者死;臣是武将不能血战疆场马革裹尸,了效忠娘娘,任凭调遣万死不辞!”他又跌跪向前。
“哈哈哈”武后爽朗笑向阎伯屿:“哀家那能容你死一万次。牛老皮更厚,你若为哀家尽忠,也要留下你的皮,包成盾,制成鞭,捍卫哀家狠狠地抽乱臣贼子。阎伯屿听旨。”
“臣在。”阎伯屿挺跪听旨。
“哀家免去你九门都督之职,待命升迁去江西洪州(南昌)任都督。”
“谢娘娘宏恩!只是……。”
“起来回话,只是什么……不妥?”
“娘娘,纪王虽已昏庸,他也对皇太子这孙女婿已有猜忌……。”
“唉!我那皇儿李弘,远非李氏大唐昔日的孝子贤孙了……。”
阎伯屿不便明言:“这……京都九门总督重职……?”
武后明言了:“九门总督之职,哀家另有任命,李贤、李显过来,给阎老都督跪下。”
李贤、李显上前疑惑地跪下,阎伯屿避向一侧,敬畏地:“老臣当不得这皇天大礼。”
武后诚挚地说:“若无你等开国元勋,哪有李氏大唐的江山社稷。而今哀家有使命相托。你若真心应允,这些龙子凤孙替李氏的先祖先王向你叩谢,你完全当之无愧。”
“娘娘旨意,臣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天恩。”
“在你赴江西洪州(南昌)之前,你必须将你的旧部老将们引见给二位太子,并带领他二人巡察驻守营地,熟悉各处城防布局。”
“臣不负王命,二位王子请起。”阎伯屿扶起李贤和李显。
“阎爱卿,你可知哀家为何将你升迁江西洪州(南昌)?”
“老臣原是先王太宗之弟滕王李元婴一同西征时的战将,滕王曾任洪州都督修建过一高阁。如今人去阁已空。娘娘也任命老臣去为洪州都督,是让老臣在滕王的阁上,享受荣华富贵。”
武后调侃道:“有福会享是真享福。你可不要像滕王李元婴仗着皇威,凭着战功,骄纵失德鱼肉百姓,政声狼藉误我子民。哀家放你去洪州,是放你这虎威尚在的老虎归山林,去镇狼狈,吓狐狸。”
“这狼狈之流是何人?”
“长孙无忌的至亲高履行。”
“这位反戈一击,背离了长孙叛党的高某,他不是远在剑南益州任司马吗?”
“再若容他在剑南纵情撒野,山高皇帝远,可能会养痈遗患了。他已升迁洪州为为刺史。你要为哀家鉴别,他是狡兔,是狐狸,还是结伙行奸的狼狈。”武后这才完成了沛王府之行的目的。
“臣定不负皇后娘娘的重任。”
“你可有他求?”
阎伯屿虔诚地起身躬请:“娘娘深知老臣行伍出身,稍有武略,缺文韬。娘娘慧眼独具,望求委派一位才学渊博之士,辅佐老臣。”
“你到是个谦逊的老将。”武后衷心褒奖:“好吧,满朝文臣任你挑选。”
太平公主按耐不住了:“条件是才华超群英俊过人,尚未娶妻的青年学士”。
李显插话:“这又不是挑女婿。”
太平顶了过去:“女婿有半子之靠,靠得住。”
李贤笑道:“若是阎都督招个上门女婿,那就有个十全十美,尽善尽美,完全可靠的辅佐亲人了。”
武后调侃道:“可惜阎爱卿不是挑上门女婿。”
阎伯屿起身奏道:“老臣一生争战沙场,年近花甲幸得一女。现已过及笄之期多年,尚且待字闺中,还望娘娘垂爱,为老臣这老闺女指婚。”
“老闺女?”武后猜疑:“莫非你这……爱女她……”
“她才高八斗有余,花容月貌,比本公主还美十分,我是她闺中知心好友,莫逆之交。”
武后正色地:“你也还是个深闺少女,不可胡言乱语,阎都督爱女,上有父命,哀家也愿为媒证于以指婚。”
“母后!”公主撒娇:“你也是个女人,应该知道女儿们的心愿。”她背诵诗文:“唯愿秋风送春暖,呵护彩蝶向云天。
断线风筝女儿命,红绳何需任人牵。”
李显调笑:“原来妹妹的红绳不愿月下老人来牵。”
公主又顶牛了:“你们男人可以随便挑三妻四妾,我们女儿家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挑个称心如意,情投意合的丈夫?我和阎都督的老闺女心意相同,不要母后指婚;红绳绝不任别人牵。”
“怎么?”武后疑道:“那风筝上落款的阎氏秀芹,原来是阎爱卿的待字闺女。”
“阎秀芹?”阎伯屿疑问:“娘娘怎知我女儿的贱名。”
“什么贱名!”公主笑斥纠正:“应该是大名,芳名阎秀芹。”
“哈哈哈”武后开怀笑道:“时也,命也,哀家你我的这两个闺女,是一对刚出炉的铁弹子,捏不住,也扔不得。你要哀家指婚,莫非你已相中哪位超群的才子。”
阎伯屿答道:“不是老臣相中某人,实在是小女喜爱王勃的诗赋文章,敬佩王勃的品格。”
公主追问:“你女儿可曾与王勃有过来往?”
阎伯屿答道:“我家秀芹严遵妇道女训,从小以琴棋书画为伴,不出闺阁从未与男子有过往来。”
公主笑道:“难怪将门出鼠女,胆小怕事连老公也不敢自己挑。王勃要是个五官不正,歪鼻子,豁嘴子,满脸大麻子的小矮子,我那天仙般的大妹子,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
武后笑道:“阎爱卿莫听他胡诌。王勃英俊潇洒一表人才,只是桀骜不驯,未必是闺中良伴,更不一定是老将军心目中的乘龙快婿。”
李显调笑:“人不作主天作主,那就来个彩楼上抛彩球,打着鸡嫁鸡,打着狗嫁狗,打着根棒锤就抱着走。”
武后笑斥:“婚姻大事让年青人议论,就没有正经话。婉儿一直没说话,你就拿个主意。”
婉儿笑道:“何不效古人,让阎老将军厅前以文选乘龙佳婿,小姐在雀屏后面挑东床娇客。”
太平公主大笑道:“真没想到你这鬼丫头,相男人,挑女婿的鬼点子也多。”
王福畤卧房病榻上,王勃正为父亲推拿。
王福畤已两鬓班白,衰老憔悴。他将王勃拉到身边,担忧地说:“武皇后对你法外开恩,今后你凡事容忍些,人言则言,得过且过。在官场,在朝堂,图得太平便是福啊!”
王勃宽慰父亲:“新城公主悲惨的遭遇,孩儿不是只字没有向人透露过吗?”
“唉!可怜的公主!”王福畤善良地感叹:“富贵莫过帝王家。帝王家除了富贵;还有什么呢?”
“人道皇上圣明,是天子,竟保不住亲妹妹惨遭杀害。”王勃与父亲同感叹:“听说皇上的两个亲生女儿,宣城公主和义阳公主还幽禁在皇城内掖挺宫中。”
“这已是朝野人所共知的事了。
王勃为证实而问:“武后逼死她们的生母肖淑妃,已经二十年了吧?”
“当年两个美丽无知的少女,而今也三十多岁,人老珠黄了。唉!”
王勃脱口而出:“武后真是个花容月貌,心狠毒辣的女罗刹!”
“住口!”王福畤急忙制止:“嗨,你又信口胡说,自己作孽,还要诛连满门啊!”
家丁进来:“请大人更衣。”
王勃忙劝阻:“父亲,你病还没有痊愈呢。”
“唉!”王福畤无奈地感叹:“武后旨意,让国师怀义活佛,在白马寺讲经说法,劝世人积德行善早成正果。我因你犯上,已贬为太常寺博士,这样的法事大典,怎能不去,更衣。”
王勃随口独自咕哝:“这个淫乱宫庭的花和尚,能讲什么经,说什么法!……
王福畤顺手给了王勃一耳光:“你还嫌我死得不快啊……!”他气恼得眼花头晕,昏昏欲倒被王勃扶住,他又狠狠推开王勃,气喘吁吁:“你,你这不孝的奴才……”
王勃低头躬身拱手:“孩儿该死,下次不敢。”
“唉唉!我这条老命早晚要送在你手中,是我自己作孽,可是你还有四个兄长啊……”
家人捧来朝服,王福畤强打精神,由两个婢女伺候穿戴。
王勃委屈地向前:“孩儿伺候父亲一同前去”。
“不用!”王福畤说罢,一迈步又步履不稳。
“父亲,让我一同去吧!”王勃又来掺扶
王福畤又推开王勃:“你给我回招贤馆去。”
王勃被闪在卧室里,从窗内看着老父亲蹒跚龙钟而去。
招贤馆内,薛华甩开唠叨的薛仁,任性地坐在靠椅上,薛仁耐心地端起一碗醒酒汤,送到薛华面前:“不要耍孩子脾气了。吴子璋亲自送你回来,你怎么能那样冷冷对待他呢?”
“你去和他亲热好了!”
“嗨,都怪你姨妈将你宠坏了。来,先将这醒酒汤乘热喝下去,冷了要伤胃。”薛华心中有愧勉强喝汤。薛仁又拿来了手巾为他拭去在衣衫上的污渍:“你该知道,王勃持才傲物,不识时务,结怨很多,是右宰相裴炎的眼中钉,肉中刺。目前虽为武皇后器重,呵护;他,终久难成大器;可能是个祸害,你怎能和他这样亲密无间经常往来。”
“是你和姨妈要我与他亲近,形影不离的呀!”
“此一时,彼一时。”薛仁耐心开导:“火能烹调暖身,也能毁家灭寨涂炭山林。”
话不入耳薛华顶牛:“嘴是两张皮,同是一个人,好人坏人由你们夸讲,污蔑。”
“同是一个人,是好人是坏人与已无关,无所谓评论他好坏。吴子璋同样是名扬京都的才子,和霭可亲有人缘,是纪王爷敬爱的雅士,是皇太子贴心的宠臣,他喜爱你诗赋,他敬重你品格,你怎么又不愿和他往来?”
“香椽再香不是桔子!”薛华厌烦地说:“吴子璋为人轻浮,哗众邀宠善于随机应变,尤其是心术叵测……。”
“怎见得?”
“近来强邀我同去饮宴,多次傍敲侧击,总是向我探听王勃与金城公主的流言蜚语。”
薛仁警惕地忙问:“你怎么回答的?”
薛华淡淡一笑:“我说,传奇无根底,越传越神奇;无稽之谈,谈也无稽。”
“回答得好!”薛仁放下心来:“叔父我不能久留京都,武后对你青睐,你定受众人爱戴,可以与权贵多作应酬,但见人只说三分话……。”
“不可抛出一片心!”薛华又任性顶撞。
薛仁仍宠爱地说:“对对。尤其要多多留神武后母子双方情况,及时向你升迁南昌的义父通报。切切不可擅自偏向一方,更不能随意成为哪一方的忠实党羽……”
“好了好了。”薛华不耐烦地顶撞:“我才不愿意掺和到他们皇家争权斗势的旋涡中去。”
“不不!”薛仁示意薛华轻声,他到门口向外张望后,将门关上插闩,机密地说:“你义父告诉我,皇太子李弘能不能继位,还难预料。武后当前权高势大,左右朝政,也难长久垂帘听政。皇上龙体欠安已是风前烛,瓦上霜;可是女人嘛当不了皇帝,帝位早晚要传统给子嗣的……”
“我才不管他们谁坐龙廷呢!”
“对!千万记牢,我们一家谋求的是荣华富贵,能永为高官,能永立朝堂。”说着他从贴胸拿出一锦囊:“这是你义父亲手交给我带来的如意锦囊。”
薛华接过这如女人定情相赠的鸡心香袋,慎重地问:“这就是你说的护身符?”
“也是我们晋升的褒荐书。更是武后母子谋权篡位,克敌制胜,都想得到的杀手锏!”
“能有这样神奇威力。”薛华欲拆观。
薛仁忙制止:“此物密封,切不可私折私观。”
“你们交给我,我该怎么办?”
“你莫露形迹,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改朝换代的乾坤帕,竟藏在你这无品位的小吏身中。”他又向窗外探望后,悄悄向薛华叮嘱:“这宝物何时出手,是私下呈献武皇后,还是暗中上交皇太子;你务必听候你义父在朝中的心腹人指示。事关重大,你要收藏好了。”
“高履行按插在朝中的耳目是何人?”
“我也不知道。”
薛华目睹手中锦囊,深感迷茫。
东宫,李弘的内殿中,他如狂犬怒吠:“滚滚滚,你们都给我滚开!”
殿的内侍和娈童都惊慌退出。
李弘一掌将纪贵妃打倒在地,又踢了几脚,吼道:“不要拿你爷爷来威吓我,他不过是我爷爷马前邀宠的鹰犬!狡兔死,良犬烹。我先祖太宗,父王高宗没斩他,给他封了王;我若登基,头一个先斩了这个倚老卖老,仗势欺人的看家老狗!……当年是他将你献给我母后,我母后才又将你塞进我寝宫当贵妃;是我向你明说了,我怕我母后,恨我母后,我厌恶母后,恶厌所有的女人,包括你也是个蛇蝎美人!”
纪贵妃哭着抬起头来:“……你,你杀了我吧!”
“不,不能这样便宜你们!”李弘心硬似铁,冷冰的说:“我要纯刀割肉万剐凌迟,让你死不了,活着更难受!你要恨,恨你爷爷奶奶,恨我妹妹,恨我母后!我当了皇帝,我要你当皇后在我面前替所有的女人受罪。……我要报仇,谁给我受了活罪,我要十倍的去报服!”……他槌胸地吼,拍着龙须案嚎啕大哭!
曹达悄悄地进来,暗暗指挥宫女扶走了纪贵妃。他又走到李弘身边抚摸着他,李弘转身搂着曹达伏在他怀中哭了。曹达轻声宽慰:“忍着忍着些吧!皇上病已沉重,你母后牝鸡是伺不了晨的……。”
内侍进来禀报:“右宰相裴炎殿外求见。”
“让他滚回去!”李弘心绪未平。
曹达以手示制止内侍去传话。抚着李弘道:“狡兔野狐还未死,怎能烹猎犬,除谋士。”
“哦,我坐上龙椅,先斩了这两面三刀的老狐狸。”他抹去泪水:“传他进来。”
招贤馆门,薛华送薛仁登上了马车,薛仁向马伕:“回府”。
马车过闹市,走进了偏僻小巷,在一府第后院停下。薛仁走了下来,感到陌生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后院门内走出曹达和锦衣卫的虎彪大汉。
曹达阴阳怪气似笑非笑:“太子殿下命我在此恭候。请!”
薛仁惶恐不安:“这……”
彪形大汉迅速逼近薛仁,怒目相视。
曹达冷冷地说;“你有自知之明,要好自为之!”
薛仁更加恐惧:“是是……”
薛仁被曹达威逼走进后院。
王勃闷闷不乐回到招贤馆,推开自己寝室,一位须发班白的老儒随之进来,深深施礼,满面堆笑:“啊,王学士,老朽恭候多时了。”
王勃答礼:“章老夫子为何在这里等候学生?”
“来来来请看。”老夫子打开一锦合:“这是老朽祖传的一双寿山鸡血石,久慕王学士才名盖世,还望笑纳,不成敬意。”
“这……”王勃有所警惕:“学生与章老夫子素昧平生并无交往,这样的稀世珍品,不敢夺爱!”
“还望尊驾成全了老朽!……”他巍颤颤跪下。
王勃急忙扶住:“有话好说,不要折杀了学生。“
“武皇后为你金盆洗冤,你是娘娘器重的……”
“不要这样说!”王勃不悦地制止。
“是是是。”老儒连忙改口:“君子自重,重美德而轻浮名,浮名是浮萍,浮云也,敬佩呀敬佩……!”
王勃不耐烦了:“你究竟要说什么?”
“实不相瞒,知恩当报,老朽是为报恩啊!”
王勃疑惑不解:“报恩?……”
“是啊是啊,老朽年过半百,一生仕途不佳。幸蒙我县父母官林县令抬举,才能来京静待圣上选拔……。”
“你要要怎样?”王勃急燥要走开了。
老儒急急说道:“我想请王学士,替我县父母官将这翡翠百花瓶,转送给龙武将军阎伯屿。我也是受人之托,知恩报恩啊!”
老儒边说,边从提篮中,取出一个紫檀木合,里面盛着一光泽晶莹,翠绿娇艳的雕花宝瓶,另取出两只金锭,又说:“这是我县父母官,赠送给王学士的书仪,黄金五十两。”
王勃虽很厌恶却不露神色:“这都为了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老儒悄悄露喜讯:“据吏部透露,武皇后要升迁龙武将军阎伯屿为洪州都督。”
王勃不掩饰厌恶了:“我与阎伯屿无来往。”
“我知道,知道。”老儒又透喜讯:“今后你与他往来就多了!”
“为什么?”
“阎伯屿是两朝的功臣元勋,有武功,缺谋略、少文才。武皇后特恩许他,在京官中挑儿位饱学之士随同赴任,他明日在府中宴请京都才子。王学士名列首位。喏喏喏,这是尊驾的请帖。”他从袖中取了请帖,双手奉于王勃。
王勃接过来,看也不看扔在桌上,十分不满:“你怎替我收下!”
“不不,适才你不在馆内,老朽认为机不可失,才替尊驾签了大名,代为收了下来。”他以为是大功一件十分得意。
“你,你收下,你去赴宴!”王勃非常恼火。
“不不,阎伯屿没有请我!”王勃拂袖转身出了卧室。
老夫子追到门口:“王学士……”他跨出室外,一想不妥,又匆匆走到桌前收拾了鸡血石,黄金和宝瓶,口中喃喃地说:“这样的怪人,世上少见!实在少见!……”,他接着宝物,连连摇头,不住咳嗽,走了出去。
闷闷不乐的王勃,在庭院内正遇见心绪烦乱的薛华,他连忙招呼:“薛贤弟!”
薛华看了他一眼,生气地扳着脸不应允,低头过去,被王勃拦住:“怎么,还在生我的气!”
薛华委屈地抱怨:“你给我受的气还少吗?”
“贤弟,你不要误会了!”
“过去你误会我,我不怨你,可现在……。”
“我也是处境不爽,心中烦闷啊!”
“你烦闷,我开心!”被娇惯了的薛华也任性了:“你清高,你洁身自好,可我已身陷污泥坑,再也不能自拔了!”他触动了自己心病,潸然泪下。
王勃诚挚友爱同情地说:“不,污泥染不了羊脂玉,你是无瑕的白璧!”
薛华更加自怜,又难以抱怨,在挚友面前孩子似的发泄:“不要你奉承我,我……我心里再也好受不了啦!”
王勃对他这纯真,委屈无奈又难明言的撒娇,不知如何劝慰:“这几天我找了你你好多回,你哪里去了?”
“吴子璋邀我同去赴宴了。”
“你,你怎能与这种人为伍!”王勃言语不自觉地生硬了。
自卑的薛华又被触到痛处,气恼地:“既已登场,就得作戏;人家骗我,我能不骗人家吗?”薛华傲慢任性地长扬而去。
“薛华,薛华……”王勃唤不住薛华,他忿恨地一拳击在大树上,无力地背靠大树,望着任风摆布的秋云,忧怨满腔:“既已登场,难道非得作戏吗?明知人家欺骗我,难道我也非得去哄骗人家吗?天哪天,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吗?这,这是一个什么世道啊!”
阵阵秋风吹得黄叶乱飞,独有秋菊迎风摇曳,花枝招展艳丽多姿。
说书人解说:王勃的悲剧性格,在人生的舞台上,何只是独自演出个人性格的悲剧。他哪知道,还有位美丽的才女,因为喜爱他的品格和文才,更因为他的孤傲任性,也正上演着一出终身遗憾的悲喜剧呀。
说书人解说时,画面中秋菊的艳姿,叠印为阎伯屿爱女阎秀芹闺房里盆景中,花瓶中盛开的繁花秋菊,秋菊又叠印成美人阎秀芹。
奶妈正指点着几个丫鬟,围绕着国色天香的秀芹,为她更衣衫,披云肩,整发饰,添钗环。秀芹却握着王勃的诗卷“剑南荟萃”爱不释手。奶妈命丫环抬来大铜镜,捧来小铜镜,夺去秀芹手中诗卷:“小姐,你迷上了王勃的诗文,你也该让王勃迷上你的花容月貌啊!”
秀芹微笑照镜看清自己的艳丽姿色,羞得以手遮面嗔道:“丑死了,丑死了……。”
奶妈笑了:“可不,我只能将小姐尽量打扮得丑一些,要不这样,让那些风流才子看见小姐天生的模样,他们当场不迷得倒下去,也都得回家去躺在床上害相思病。”
“奶妈……”秀芹偎在奶妈怀中轻拍轻打。
“来了,来了!”小丫头喜鹊叫着跑了进来。
奶妈问:“谁来了,喜鹊?”
“你叫我去打听的那个;小姐嘴上念的,心里想的大才子王勃呀!”
“哟,他来这么早?大概知道我家老爷要挑上门女婿吧!”
“奶妈……”秀芹羞嗔地离开。
“这样的好事,喜事谁不知,我溜到花厅,亲眼看见的,这么早早的来了好多,好多。”
奶妈斥道:“你这个歪嘴喜鹊乱报喜,王勃只有一个,哪能有好多,好多!”
“我要说谎,就让我嘴上长个大疔疮!”小喜鹊又喳喳说个不停:“真的来了好多好多年青漂亮的公子,我看个个都象王勃!”
奶妈:“你以前见过王勃吗?”
喜鹊:“没有见过也能想得到,能写好文章,长相准漂亮。”
奶妈:“那好,以后开科你当主考官,不看文章看长相,就保准能选出状元郎来了。”
喜鹊分辩:“文章我看不懂,看人看得准。后来,王勃真的来了。那个俊美,那个漂亮,所有的俊俏公子,谁都比不上。我看了又看,看也看不够,要不是来送信报喜,我真想盯在那里看个饱!”
丫头,奶妈听得又嘻嘻轰轰笑了。
“死丫头,看你说得人心里馋馋的。”奶妈又笑道:“你怎么知道他就是王勃,王学士?”
小喜鹊自作聪明,自夸讲:“我不能问,还会看,更可以听嘛。王勃一进花厅,满厅的才子都围着和他谈笑,夸他文章天下第一,而且传遍了天下。这不是吗?看,都已经传到小姐手里来了!”
秀芹装着气恼:“你还要胡说!”
小喜鹊指着秀芹手中的诗卷:“这也是我胡说吗?”
妈妈拦住了追打喜鹊的秀芹:“小丫头,你还有没有个尊卑上下呀!快快,快些帮着小姐打扮吗!”
奶妈,小喜鹊和丫坏们,为秀芹最后披上轻纱飘带。
盛妆的阎秀芹在丫环奶娘的簇拥下,走下秀阁,走在盛开的秋菊中,池中鸳鸯戏水,枝头黄莺和鸣,秀芹喜在心中,眼前园中秋色映在她脸上都成了春光。
说书人画外音:“情窦初开的少女,都对爱情有美的幻想,幻想又都寄在婚姻上。可是婚姻并不是追求的美好的幻想的结晶,现实总是那样捉弄人啊!”
小喜鹊又在花丛曲径中跑来了:“小姐小姐,王勃被老爷请到书斋去了!”
奶妈急问:“是单独请进书房的?”
“那还能假,是我亲眼——偷偷盯着看见的。”
阎秀芹故作正经:“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妈娘也调笑道:“是嘛,你小喜鹊少见多怪,丈人选女婿嘛,这是用不着你急。可也是的,老爷挑女婿比小姐还心急!”
“不见得!”喜鹊顶嘴:“老爷是急在脸上,我小姐才真正急在心里!”
“要死,你们……”阎秀芹被羞得扭头转去,被大家拉了回来,小喜鹊调皮地在前面拖了。
阎伯屿的书斋。
阎伯屿从吴子璋手中接过翡翠花瓶玩尝。他高兴地说:“南昌县令这厚意,老夫不能笑纳。好在我即将去洪都赴任,到那时这位老土地,能鼎助一臂之力就比这宝瓶更贵重了。”
吴子璋接过宝瓶:“老将军高风亮节,是学生表率!”
家僮进来:“太平公主褒荐的那位剑阁才子薛华请到。”
阎伯屿喜上眉档:“快请进来。”
家僮向外:“有请薛公子。”
薛华飘然而入,潇洒地叩拜:“学生薛华参见龙武大将军。”
阎伯屿眼前一亮,抢步上前武将风度,用双手有力地托扶起薛华,定眼打量后道:“难怪太平公主在开出的花名册上,特别褒荐了你。高履行可是你的义父。”
“愚生不才,正是他的螟蛉之子。”
“难怪他褒举不避亲。”阎伯屿亲切地拉着薛华悄悄说:“你比他给的信中夸得还好。”他一把又拉着吴子璋道:“吴子璋,这又来了位貌似潘安与你比美的,这下一步该你们显显,谁的才同子建了!”
阎府正厅里,迎面一座孔雀开屏的锦绣屏风外,十几位年青英俊的紫袍儒雅之士,三五成群散在厅内谈笑生风。
厅外有人宣报:“龙武将军驾到。”
众青年学士纷纷待立两侧。
妈娘,小喜鹊和丫环们拥着秀芹,乘众人面向外迎接阎伯屿之际,从花厅后门悄悄来到雀屏后面。
阎伯屿武将风度右手携着吴子璋手腕,左手有力的握着薛华手腕,虎虎阔步进入厅堂,向恭候的学士们抱拳施礼,宏亮豪爽笑道:“诸位久候了。”
众学士纷纷躬身拱手答礼:“阎老将军健康长寿。”
喜鹊早在吴子璋薛华进来前,就轻轻向阎秀芹告诉:“王勃来了,王勃来了!”
秀芹立刻制止了喜鹊叫唤,捏了她一下。
奶娘问喜鹊:“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喜鹊越看越糊涂:“左边的……右边的……都像是王勃……”
秀芹嘴角含笑又轻轻敲了小喜鹊一下。
阎伯屿正中归座在红木画屏前。
学士们先后发现屏风后花技招展,隐隐约约站着一群美人。他们都有点魂不守舍,恨不能看个清楚。
阎伯屿早已察觉,坦率地笑道:“阎某今日宴请六部九寺和学府,院馆年青的紫袍学士,实不相瞒是要选个入赘的乘龙佳婿。”
大厅中屏风后一阵嘻笑骚动。屏风前个个学士喜形于色。
阎伯屿武夫气慨又说:“阎某一生戎马生涯,曾随先王西征,又奉圣命镇守京都九门,是个缺文韬的武夫。而今一心要招个有才有貌的女婿。可惜我老年得娇女,深闺只一人。若有一二十个女儿;你们这些英俊年少的才子,我就全都招赘入府了。”
学士们被说得忍俊不禁,哄堂大笑。
屏风后也扬溢出一阵笑声,喜鹊更是笑得轻轻鼓掌。阎秀芹狠狠捶了她一下,转身欲走。奶娘追着拦住:“你还没有弄清哪位是王勃呢?”
秀芹略一停顿说:“你们盯准了那头两位交试卷的学士……。”她羞涩地向奶娘轻轻耳语。奶娘频频点头笑道:“放心放心,包在我的身上。”
屏风前阎伯屿起身道:“这里是小女冒昧不才,出的试卷。诸位先试文才,然后由我父女再相品貌。”
屏风后,秀芹匆匆离去,丫环们也尾随走了。正向前盯视入神的喜鹊,回头一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焦急地喊:“小姐……”
奶娘一把拖住小喜鹊,也在她耳边轻轻吩咐,喜鹊高兴地说:“哦哦……第一第二头两个……误不了,更错不了!”
奶娘和她又在屏风后盯牢了。
厅堂内,众学士正按阎家父女的命题作文章,有沉思者,有低吟者,有人拂纸醮墨难以落笔,有人疾书中断,索尽枯肠难以成篇。吴子章和薛华端坐行书,目不斜视,有缓有急由心畅书。
长安朱雀街闹市中,行人熙熙攘攘,王勃独自踯躅在人群中排遣郁闷。
数声尘鞭鸣响,行人小贩纷纷避在街旁。
行人妇女:“今天护佛大国师又要在严华寺讲经说法了。那位剑川迎来的护佛圣母,不知道抬不抬出来显法身法相啊。”
行人老者:“就看我们有没有这缘份了。”
女小贩:“我有缘见过,又端庄,又美丽,我这辈子头次见到,真是天仙。”
行人老者:“听说这圣母活佛,活灵活现像我们的武皇后娘娘。”
王勃挤上前问:“这位护佛圣母在哪里?”
行人妇女:“严华寺听经也许见得到。看你有没有那缘份了。”
“有有,我们都有,你们听有这样的仙乐,准定又抬圣母沿街受朝拜了。”老者合掌而拜。
阵阵丝弦管乐法器。飘来由远而近悠扬悦耳的梵音妙乐,龙武军策马开道,随之一列锦衣侍者洒水静尘,散花铺路。稍时远远传来笙箫鼓乐,一排小沙弥,青年僧人,打着佛旌神幡,捧着经卷法器,敲打吹奏着乐曲,列队缓缓而来。金寡妇已是锦衣绣袍,金色佛冠加顶,脸色苍白微闭双目,坐在十人扛着的精制抬阁中,后面是骑着白色骏马的健壮彪悍相貌堂堂的国师怀义方丈。夹道而观的百姓先后纷纷跪地,合十参拜。后面行人争相合掌观望,挤来挤去又都不敢向前拥。金寡妇被抬过王勃身边,王勃冒然喊了一声:“金大嫂!”她眼没睁,呆如木偶,毫无反应。王勃无形中成了众目之的。被群众的目光威摄下不能再大声呼喊。
王勃向老者:“老公公,还有个灵童在哪里?”
老者合十对答:“神在天上,佛在心中,灵童是佛下凡尘,普渡众生脱苦海,你虔诚求佛就能见到。”
王勃追问:“请问你哪里见过灵童?”老者闭目合十不答,王勃又问:“请问你哪里去找灵童?”
老者不耐烦厌恶道:“灵童是活佛。我和你无缘,佛与你更无缘。”老者避开挤上前跪拜了。
阎府正厅,学士们都在绞尽脑汁,想博取阎伯屿父女的青睐。
家丁进来向正在品茶的阎伯屿禀报,阎伯屿勃然含怒:“哦,他好大的架子!”
吴子璋首先完篇来交文稿,关怀地问:“阎老将军为谁生气?”
“王勃!”阎伯屿怒形于色:“老夫两次三番差人去邀请,他竟敢避而不见!”
吴子璋轻蔑一笑,不伤皮肉暗伤骨说道:“他呀,天生个牛脾气;对皇太子殿下也敢忤逆傲慢,他是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大文豪呀……”他见薛华前来交稿,收住了是非议论,争先交上文稿:“学生拙作,请老将军指正。”
奶娘向喜鹊交待:“哪位是交头卷的,哪个是第二位。你别弄错了。”
喜鹊抱怨地顶嘴:“这是小姐的终身大事,谁敢弄错了,我又不是蠢驴……”
妈娘连忙制止她大声说话,喜鹊吓得伸舌头。
薛华随后呈上稿卷,阎伯屿客气地说:“请厅外用茶。”
薛华恭敬施礼退出厅去。
阎伯屿拉过吴子璋又问:“王勃果真脾气这样培养乖张孤僻?”
“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故意装出有话难言:“我不愿说他的孤傲狂妄。”
阎伯屿质疑咨问:“为何武皇后对他如此器重……?”
“可是至今让他赋闲,并没有重用过。”
“由此可见他的为人……。”
吴子璋又伪装避讳:“不过我……虽与他有过往来,不是深交也,也难以深交……。”
“莫非……”阎伯屿更加疑惑要追问到底。
吴子璋自高自拔,不惜伪言:“人以群分,我俩话不投机,半句也多!”
阎伯屿以问作结论:“此人一定嫉才妒能。”
“学生不敢这样评论。”吴子璋有意误导:“只怨学生不该答应他父亲王大人请求,代他写了那篇碑文,偏偏圣上又赏赐了千两黄金,嗨……”他悔恨地样子长叹了一声:“唉……!”
阎伯屿被煽动了斥道:“这狂生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不”吴子璋十分谦逊:“是学生才疏学浅,不愿向他高攀。”
阎伯屿粗心大意;“幸亏他没有应邀来赴约。嗨,偏偏小女秀芹偏爱他的文章。”
严华寺庙会人山人海。寺门前更是佛旌神幡林立随风翻飞。王勃赶到寺院门口被几个护寺武僧拦住。
武僧:“这位施主寺内怀义国师正在讲经说法,寺内善男信女已满,无立足之地,施主向善,改日再接善缘吧!”
王勃恳求:“我要见圣母和灵童。”
武僧:“活佛灵童临凡尘初遭劫难,还无下落。”
王勃急了:“怎么灵童遭难了!”
武僧:“圣僧唐玄藏,去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今这位活佛灵童才初遭劫难。以后必然经一次劫难,多一次惮悟,遇难成祥就多一层佛光。”
王勃:“哪,我先见见那位圣母。”
武僧:“护佛圣母不是信徒想见就能见的。”
王勃:“我有要事今日一定要见。”
武僧:“来啊,将这凡夫俗子赶离山门外。
武僧们前来推拉,被王勃纷纷打倒。王勃冲向寺门。一龙武军尉拦住:“王勃,这是武皇后上香的严华寺,佛门重地清净所在,你不可任性胡为?”
王勃:“你怎么知道我是王勃。”
“你是狂妄孤傲的才子,朝野上下谁人不识,你要见护佛的圣母,可去城外尼庵她修行之处去朝拜。”
“他住哪座尼庵?”
“佛无定居。你也学唐僧西天取经,出西门先向西方去找吧!”
“一定能见得着吗?”
“就看你有缘没缘了。”
“就是有缘,就是有缘啊!”奶妈拿了头两篇文稿到问琴斋见了秀芹就说:“这头篇是左边那才子的,第二篇是右边那位才子的。这两位果然才貌都拔了尖。小姐你看看哪篇是那王勃的!”
秀芹羞答答地说:“这是匿名试卷,不写名字的。”
“现在分不清也不要紧。”妈妈有把握地说:“我已经让喜鹊按小姐吩咐行事了。”
秀芹担心说:“该不会弄错了吧。”
奶妈铁板上钉钉子:“小姐亲眼看,亲自挑,哪能错得了!”
小喜鹊在花丛向书僮耳语后,将他推了出来,迎向随家丁的引路的薛华。书僮上前施礼:“公子有人邀请,请随我来。”
喜鹊喜滋滋前面远远走,书僮引着薛华随后行。
说书人:是人缘是仙缘是姻缘,有缘无缘,因何缘故呢?王勃城外寻找圣母金寡妇,秀芹府内挑选乘成龙婿王勃。错中错后果如何,是喜剧,是闹剧,但愿是大团圆的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