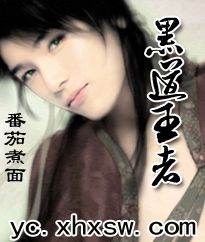正文 -- 第十八集鸣翠阁上秋夜长
第十八集鸣翠阁上秋夜长
说书人慨然而说:据说人死了变鬼,鬼是人变的。可总是人怕鬼,没听说鬼怕人。尤其是那些弱者,他们无权、无钱、无力,活着没有能力反抗,只能以死相拼。死了还没有能报仇雪恨,变成了孤魂野鬼也要找冤家对头。像熬桂英活捉王魁的恐怖故事太多了,也太恐怖。不过那都是传说。
王勃一伙人在伐木场碰上的鬼就不同了,他们都是被官家强征徭役,活活冤死的,官家就是他们冤家对头。在这群冤魂野鬼中,王勃这伙人,就是他们复仇的冤家,活捉的对头,这仇人相见,怒火中烧,分外眼红的情景,能不触目惊心,万分恐怖吗?”
牵马老叟紧紧抓住了笼头高叫了声:“冤魂出来了,快逃啊!”
憨儿和两个武士回头欲逃,王勃吼了声:“不要跑!”这伙人站住了。
刹那间,高大的无常,乱窜的冤魂消失在夜雾弥漫的乱葬坑中。
恐怖笼罩了整个山谷,寂静,压迫得人透不过气来。枯树、灌木、丛林、怪石,在人们的眼中,都幻化成了奇形怪状狰狞的鬼怪。
残缺月芽儿的银辉,映得漫地轻雾滚滚四溢,几处坟堆中断续喷出似烟花的星火,影影约约,大小鬼魅又在坟野中隐现……
猿声悲啼,饿狼哀嚎,枭叫,虎啸,远远近近,断断续续从四山深谷幽暗中飘来,尤其乱坟中凄惨鬼哭,悲戚沉沉,更刺得人心紧缩。
突然,陡峭的山崖上,滚下一些大小岩石,王勃的一行人,吓得四处躲藏,逃奔。
“不要乱动!”王勃拔出了白鹤剑,寒光闪烁。
白发老叟脸色突变,将川马勒得更紧:“不要惊了马!”
惨淡的月光下,乱坟堆中升起几柱湿柴冲出的白烟雾,远远又隐隐绰绰移动着一群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的魅影。磷火在远近滚动飘浮……
王勃翻身下马,持剑向乱坟堆走去。
“站住。”老叟脸色惨白,拖住了王勃:“那是些冤魂野鬼。”
王勃凝视着惊慌失色的老人:“冤魂野鬼?……”
“冤魂……是屈死的冤魂,他们都是被官家抓来砍伐树木,被打死的,逼死的,活活饿死的冤魂哪!”老人干枯的眼中闪灼着悲戚的泪光。
“……是冤魂……”王勃垂下了剑,从深心发出悲悯同情的感叹:“都是冤魂啊!……”
“苦哇……苦噢!”接连几声悲切凄厉的鬼哭,崖上立即有阵阵沙石滚下,高处又飘来一蓬蓬随风飞舞的黄叶,那瘦长的黑影,又在坟堆后的草丛中出现,大大小小的鬼影,从坟堆四处向王勃这伙人慢慢逼近。
“快逃啊!”老叟牵马回头就奔。
王勃提剑纵步追去,勒住了矮马,逼住老人:“不许动!”
憨儿等一伙扔下行李的人,也被同时喝住了。
那群冤魂却发出啾啾怪叫,还是从远向近逼来。
王勃拾了块石头,嗖地向那瘦长的无常扔去,只听见“啊——!”的一声惨叫,黑影倒下了,从高坡上滚了下去,带得沙石哗哗响。
老叟扔下了缰绳,疯了似地惨呼:“么娃子啊——!”他踉踉跄跄向黑无常倒下的地方奔去。
那群冤魂和野鬼也停止了前进。
王勃挥动寒光闪闪的白鹤剑,冲向乱坟坑,两个卫士和憨儿也执刀,持棍随了过去。
群鬼纷乱窜逃,跌跌绊绊,发出了女人的惊叫,老人的惨呼,孩子的啼哭……。
憨儿随王勃奔到黑无常倒下的地方,只见坟堆后倒着一根长竹竿,上面顶着一破竹筐,筐上缀着破麻皮,烂藤条,竖起来远看活象个黑无常。
卫士吴大胆从坟堆深草丛中,抓起一个跌倒的小鬼,他举刀要砍,被王勃纵身跃来托住。王勃掀掉小鬼头上罩着的破篓子,站在月光下的,竟是一个衣不遮体,光着屁股骨瘦如柴的孩子。他吓坏了,两只大眼睛充满了恐惧,惊慌,要哭了,又不敢放声……。
“狗娃子——!”一个妇女披头散发,惊呼惨叫疯狂地奔了过来,紧紧将这孩子搂在怀里,母子惶恐地望着王勃。
“妈妈——”又是两个头发散乱的小女孩追扑过来,紧偎紧护着面目憔悴的妇人。妇人又急忙护着哭泣惊恐的女儿,她一双手护不过来,不顾一切用身子挡着,四双眼睛绝望悲哀地瞪着王勃,十分惧怕地望着他手中寒光闪闪的剑。
“饶命啊,长官!饶了我苦命的娃子啊……”妇人满脸泪痕。
“妈妈……”那男孩终于憋不住嚎哭出来,两个女孩随着放声哀啼,母子四人都呜咽悲啼成一堆……。”
王勃垂下了剑痛心地问:“你们这是……。”
妇人泣不成声;“我们是饿的……是饿的呀!”
“憨儿,拿干粮给他们。”王勃插剑入鞘。
孩子们接过憨儿给的糕饼,狼吞虎咽象群饿兽。
霎时间,乱坟丛中冒出了饥饿的人群,他们扔了扮鬼的各种破烂,三五成群畏畏缩缩,前前后后跑拢来,又先后纷乱跪下伸手乞讨:“长官给我点吧!……”“老爷给我点吧!”“救救命啊!”……一群衣不遮体,被饥饿折磨得变了形的;不是鬼,是群枯瘦病弱的老人、妇女和可怜的孩子……
惨淡凄凉的月光下,王勃悲怆地望着这群似鬼似人,非鬼非人饥饿的人群,他茫然了,僵立在他们中间,望着乞求悲哀的眼情,望着枯稿乞讨的手,他泪水盈眶而出……。”
王勃由衷发出沉重的心声:“天哪,……我能救济得了这么多贫苦的黎民百姓吗……我就是八方巡抚,能拯救得了满天下,这样多冤魂野鬼吗?……。”
王勃心声中叠印出以下画面:王勃一伙人迷路了,盲目地穿行在丛林,山谷和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中。
憨儿牢骚地:“赶路赶路,不住鸡鸣早看天的野店,偏要跟着那个领路的糟老头子,真正碰上了活鬼了。”
吴大胆叹气道:“如今迷了方向,这路可怎么走啊!”
贾老虎泄气地:“不被豺狼生吞活吃了,是我前世里积了德……。”“你不是老虎吗?”“我是贾老虎!”两卫士边走边抱怨。
王勃默默无声,牵着川马,挥剑斩断荆棘老藤,开着路前进。忽然听见流水声:“前面有溪流,水向低处流,溪向山外走,跟上!”
王勃领着一行人沿小溪探索前进。远远沟豁中,一点火光忽隐忽现,憨儿一惊:“鬼火!……”
王勃定神一看:“前面山谷有人家。走!”
他们碰碰撞撞过了溪流,穿出丛林,火光越来越近,远远听见女人嘤嘤哭泣声。
一丛野竹林中,泉水边一堆篝火熊熊,不见人影。
“有人吗?……有人吗?……”王勃向四周呼唤。
除了猿啼狼嚎,潺潺流水声,寂静无有人答应,王勃持剑向灌木丛搜寻。刹那间一个蒙面人从身后持木棒向他猛击。他迅速闪开,这人又拼命向他拦腰横扫。王勃反手挥剑将木棒削去一截。这人一怔,并不逃走,竟又用半根木棒再攻王勃,又被王勃一掌推倒。
憨儿等人正要去合击,王勃立刻拦住。
显然,这蒙面人一再拼命,根本不是王勃的对手,他从地上爬起向溪流逃去。
“站住!”王勃边喊边追。
这蒙面人并不停步。王勃追得快,他逃得快,追得慢他逃得慢,王勃停他也停。王勃已识破他是在误导,别有心机。于是他故意停止追击,回转身再向篝火处奔去。
果然,这蒙面人又追向王勃攻击。王勃回身,顺手牵羊夺下这人的木棒,两个卫士将他抓住,王勃扯下了蒙面的破布,原来是领路的白发老叟。卫士们以刀逼住了他……
“爷爷——”一声悲痛的惊呼,草丛中岩石后站起了一个半裸的少女。她仅穿着一件坦胸露臂破旧的胸兜,月光照着她美丽脸,眼中泪光闪闪,满布着惊恐,焦急,忧伤神情。她双臂交叉护着洁玉的前胸,象一座美丽的雕塑。
老人不顾刀剑,挣开卫士,踉跄冲到少女身边,脱下自己破衫裹住少女,将她推到自己身后。他赤手空拳,怒目圆瞪准备以死相拼。岩石后有人呻吟,少女悲痛地喊了声:“么娃子!”立即跑下岩石。
老人也发出悲惨的嚎哭,也随着奔下去。两块岩石大裂缝的乱草丛中,一个双目紧闭的孩子,身上盖着一件补过的旧花衫。老人少女扑在他身上叫唤痛哭:“么娃子,么娃子……”悲痛已使他们忘了身外的一切。
王勃一伙人被眼前的情景触动了,静静站在周围。王勃脱下外衣披在老人身上,老人和少女疑惑地望着王勃。
王勃将孩子托抱到篝火边,他运气推拿,针刺穴位,孩子从昏厥中醒了,微微喘息,蠕动……。
老人和少女相依着一直盯视王勃治疗,这时情不由衷地搂住孩子叫唤:“么娃子——!”
王勃继续替孩子伤口上洒药,撕下内襟包扎,憨儿象护士在旁相帮,两个卫士主动地为篝火加柴,火焰熊熊,一团暖光照耀着这伙默默无言的人们。
东宫太子内殿,裴炎、周正良和几个李弘的心腹散坐在周围,紫铜暖烘炉旁,曹达和几个内侍,伺候着李弘脱头盔解铠甲,他十分不耐烦,脱靴时猛一收脚,将曹达闪坐地上,口中还愤慨地骂道:“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
曹达爬起来,又伺候李弘更换便服,被李弘用力推开!怒斥:“你们将我妆扮得再威武,我也是个丢盔卸甲,不堪一击的窝囊废!这下好了,东征结束了,今后再怎么招兵买马,没了兵权,怎么去谋政权!……”他恼火地躺在了卧椅上。
众人鸦雀无声,听着他谩骂,望着发火。稍时裴炎终于笑道:“东边下雨西边晴,风云变幻难料定。难料定,还是可以料定,皇后她还得遵从王命。殿下今日这样体体面面,热热闹闹地胜利班师回朝。万众欢腾夹道相迎,谁不夸皇太子殿下威风凛凛,英武俊美,不愧是即将继皇位的君主。”
“得得,这身钢盔铁甲没有将我累死!”李弘不满地抱怨:“继位,还不知哪年的皇历上才有这黄道吉日,你这个事后诸葛亮,还是早拿个主意,今后该怎么办?”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就是说清晨东边失一点,傍晚西方收一片。成败得失的转换有个时间和机遇,操之过急更多失误。”
李弘不耐烦:“废话少说,我听你的扮演了常胜将军,再该演出什么戏了。”
裴炎夸赞道:“殿下是云中真龙,露头不露尾已是名扬天下。犯不着假戏真做去讨喝彩,而今殿下仁孝美名四海传扬,威武智勇传扬四海,尽可以安心养歇,以逸待劳,等待时机。”
李弘不理解:“现在不监军了,还有什么时机可等。”
裴炎提示:“殿下该知;蝼蚁之穴,可以……可以决于千里之提,你要我利用小小蝼蚁……?”
裴炎微笑:“等时机不如造时机,殿下可以不寻蝼蚁,养白蚁。”
“你要我培养白蚂蚁?”
“多多培养白蚂蚁!”
李弘略有所悟:“白蚂蚁可以蛀栋梁……栋梁蛀空,可倒楼房,你是要我……”
裴炎点明:“暗中培养白蚁之穴。”
“这蚁穴何处找?”李弘急忙追问。
裴炎问道:“这有一窝,殿下可记得那高履行?”
“高履行?”李弘答道:“他是我舅公长孙无忌夫人的二弟,论辈份他也是我的舅公公,我不但认识,早年也有往来。”
裴炎道:“他因为是长孙家族中得力的一员,早些年就被你母后排除异己时,贬到剑川去了。”
“这我知道,他该年过花甲了,怎么,他还没有被折磨死啊?”李弘回忆道。
周正良插言道:“这个花花老头,升官了,荣耀得很呢。”
李弘疑惑地问:“我母后肯留下长孙家族这条祸根?”
裴炎指出要害:“皇后娘娘一贯善于利用酷吏除脏官清异己。高履行能被她留下重用……”
李弘聪明领悟道:“准是以毒攻毒!”
裴炎推断:“你母后将杜微贬谪剑阁,那是明谪暗保。”
李弘:“怎见得?”
裴炎:“若不是保,这小子在高履行手下早就见了阎王爷。”
周正良补充:“如今又将王勃也贬谪到剑阁……”
李弘:“这分明也是明谪暗保。”
裴炎:“是与不是,还不能早下定论,反正可以料定,王勃之流,流放剑川,不是去与高履行同流合污,就是让他们相互监督。”
李弘也料定:“万变不离其宗,剑川这是我母后在西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贼窝。”
裴炎道:“不管如何,王勃总是皇后娘娘手中一粒能堵棋眼的得力棋子。”
“哼哼!”李弘咬牙切齿地说:“山高皇帝远,本王决不能让王勃这个马前卒,充当头炮来将我的军。”
裴炎阴冷的说:“除掉这小子不难,殿下也来个以毒攻毒!”
李弘笑道“对,我们也将高履行这个老狐狸当成白蚁养,将我母后的贼窝变成我的白蚁穴!”
裴炎向周正良:“周侍郎,你去过西蜀征用造战船木料,把以前与高履行打交道的情况说说。”
周正良兴致勃勃地说:“那个高履行啊……”
李弘这一伙心腹全神贯注听介绍。
群山环抱的山谷中,山花盛开,清泉哗哗地在大小卵石中流淌,憨儿和几个赤条条的娃子们,在一泓明彻的碧潭中戏水,负伤的么娃子坐在大蘑菇石上向憨儿浇水。苦妹子和那小鬼的母亲,在一块大卧牛石上,为王勃他们洗衣衫。两个卫士在远处钓鱼。
画外王勃沉吟:“
江汉深无极,梁岷不可攀。
山川云雾里,游子几时还。
镜头推出王勃,身背药篓立于山崖上极目远望,放声吟唱。稍时二个老叟也跟了过来,拿着药草相问,王勃一一指点,细细解说道:“这是七叶一枝花,是治毒蛇咬了,医治最好的蛇药。山中生百草,百草治百病。你们可以靠山吃山哪……。”
么娃子指着王勃,问正在擦干身体的憨儿:“王大人刚才在做什么?唱山歌?”
“不,他在做诗。”
“做事?他这是做么子事?”
“么子事?什么叫么子事?”憨儿不懂川话:“我家老爷子是诗人,做的诗好得很。”
么娃这才闹明白:“哦!他和我姐一样噢。”
“什么,苦妹子,你也会做诗?”
苦妹子笑得低下头,羞涩不语。
“当然嘛!”么娃子骄傲地又说:“要不是让官家抢走了,我马上就拿给你看。”
“哪个官家还抢诗?”憨儿更呆住了:“哪,你姐的诗,比我家老爷的诗还好。”
“啷嘎哟!”那婶子笑道:“你们是把包龙图当了灶王爷吧,分不清神和人了!苦妹子是养蚕抽的丝。”
么娃子还逞强:“我们这里男的是不抽丝的!”
“嗨,我和你这没喝过墨水的说不清楚。”
“啥子?你说啥子?”
“傻子!你和我一样,我不聪明,你也够笨的!”
那婶子笑了:“木鱼咧嘴笑木瓜,两个傻瓜蛋。”逗得苦妹子大笑。刚擦干了身子的憨儿,被么娃子和几个光腚的孩子又推到碧水潭里,孩子们拍手喊叫:“滚你个傻瓜蛋?”接着唱童谣:“
木鱼笑木瓜,长得不好看。
木瓜敲木鱼,臭得像头蒜。
木瓜木鱼、木鱼木瓜干、干、干,
打胜的是傻瓜,败了是个傻瓜蛋!”
秀丽山谷中洋溢着孩子们的笑声。穷人也不总是愁眉苦脸,像久旱的土地,只要有场阵雨,花草树木就生气勃勃了。孩子的童谣笑得溪水也伴着游鱼欢跃歌唱。两个卫士钓了条大鱼,更引得小叫花子样的孩子,追追赶赶,山谷成了欢乐的天堂。
王勃在溪滩的石崖上,指导老叟和苦妹子晒草药。
么娃子和孩子们又在和憨儿闹着玩。么娃子扒在憨儿背上问:“你们都不是官家人吧?”
憨儿憨态十足,伸出了大拇指:“怎么不是?当然是!我家老爷是二太子沛王爷的侍读呢!”
苦妹子靠近了一点问:“侍读?侍读是个么子官?”
“侍读,侍读……”憨儿一时蹩住了:“哦……!侍读就是陪着皇帝的儿子读书。”他聪明地又补上一句:“和我一样。”
苦妹子惊讶地:“你也陪着皇帝的儿子侍读?”
“不不,我侍候我家老爷读书写字。”
么娃子肯定了:“哪,你也是大老官了?”
“嗨嗨,我芝麻点小小毛毛官也不是。”
“哈哈,我早晓得你扯谎。”么娃子大笑道:“我早就算出来了,你们都不是官家人。”
“是官家人,我们真正是官家人。”憨儿憨里憨气拿不出证据地解释。
“官家人?”么娃子更憨直:“吹牛,吹牛!哪有你们这样的官家人?不骂人,不打人,不抓人,也不抢人家的东西,还把东西送把人!”
苦妹子晒翻草药笑道:“官家人,有坏人,也有点点好人。”
“对,我和我家老爷都是好人。”憨儿憨笑。
苦妹子微笑:“你老爷,他一点都不老。”
憨儿憨憨地说憨话:“是嘛,我家老爷是不老,没有娶老婆总是小。”
苦妹子羞得满面通红,走了几步又回头问:“你家老爷叫么子名字?”
“王勃。”
“王勃,他就是王勃?”苦妹子站住了,怔怔自语:“他不一定是王勃吧!……”
憨儿发了憨劲:“什么他就是王勃。王勃就是王勃,这还能掺假的。”
苦妹子眉头紧蹙,不理憨儿,药也不晒了,匆匆忙忙奔向崖洞。
崖洞前,王勃指导着那位老叟和另两个老人正尝草药,讲授草药的功能:“……五谷杂粮也属百草人,吃五谷杂粮生百病,治疗百病靠百草,百草百草长在深山都是宝,不认识才是一文不值的杂草!”
老叟应承道:“是啊,是啊,漫山遍岭都有宝,就看识不识,找不找。经大官人这一指点,我们也有了个正正当当活路了。”
苦妹子过来喊开了老叟,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将一封信塞给老叟。
老叟走向王勃问:“王大人,你是京城来的吗?名字是不是叫王勃?”
“是啊!”王勃疑惑地。
“你犯王法了?犯的什么罪?”
“我没犯法,没有罪过。”
“是升官?”
“不,我得罪了王公贵胄,是贬谪到剑阁的!”
老叟叹道:“唉!这就对了,怎么看你也不像个坏人,不像个奸臣。我看……你不要去吧!”
“为什么?”
老叟叹惜地:“过了剑门关,你就进了鬼门关,入了枉死城啦!”
王勃十分疑惑追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先王太宗的东宫太子李承乾,你知道吗?”
“他是当今皇上的同胞长兄,原来是太宗皇位的继承人。”
“他被贬为庶人当老百姓,流放到黔州受苦不说,最后是被他一个远房舅舅弄来剑川,死在剑阁的。”
“这,我知道。”
“还有个新城公主,你知道吗?”
“她是当今皇上最小的妹妹,她已经死在京都了。”
“她的男人附马爷,也是流放到剑川,被县太爷活活打死的呀!”
“这,我也知道。”
苦妹子忍不住插嘴了:“哪,你为什么还要活活去送死?”
王勃泛泛回答:“我不是龙子凤孙,皇亲国戚。我又不争权夺势谋王篡位。”
老人不懂王朝复杂的斗争,他只从个人的关怀又问:“你在京都有没有仇家?”
王勃诧异了:“难道有谁也要谋害我?”
苦妹子急了:“爷爷,把信给他嘛!”
王勃接过老人的信阅读。
老叟向苦妹子说:“……那天两个差官谈谈说说,是说的要谋害的人叫王勃,是他吗?”
苦妹子说:“菩萨保佑,但愿信中写的不是他!”
“好狠毒的皇太子!”王勃愤懑地问:“你们这封密信是哪里得来的?”
苦妹子答道:“在伐木场的乱葬坑。”
“送信的差官呢?”
“恶人有恶报!”苦妹子笑道:“他俩调戏我们的小寡妇,被引到乱葬坑,让活鬼们吓得胡窜乱跑,跌下溪坑淹死了。他们信中提的王勃是你?”
王勃苦笑道:“只能是我。人生在世谁无死,听天由命吧!”
王勃的画外音,深沉地念道:
剑门关哪鬼门关,鬼哭狼嚎人心酸。
深涧流的思乡泪,奈何桥通阎王殿。
活也难,死也难
死活都要进这剑门关哪!”
镜头推出剑门关景色,双峰相峙古木参差,袅绕云雾沉浮于山腰,王勃与杜微牵马并肩踱上剑门关。杜微笑道:“刚上剑门关,你就心酸了。子安贤弟,你怎么多愁善感起来了?”
王勃淡淡一笑:“这是那领我活见鬼的老人家,念出的心里话呀。”
“是嘛。”杜微宽慰道:“山深多瘴气,专门毒煞忧天的杞人,瞧我不是活得好好的,不用在歧路,又儿女共沾巾了。”
登到关上,遥见群山层峦叠嶂,屹立于茫茫云海,一轮旭日放射火红光茫,给无垠宏宇渲染上变幻的色彩。
王勃笑道:“昔年相别灞桥赠柳枝,今朝欢聚同过剑门关。”
杜微也笑道:“贤弟诗云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哪,胜过了三味真‘言’了,哈哈哈”
二人立于关上俯视壮丽景色,剑阁县城遥遥可见,好似在山花柳丛中,王勃油然生情,随口成韵,他快步浏览景色,欢快嘹亮地吟颂:
物外山川近,晴初景霭新。
芳郊花柳遍,何处不宜春。
杜微拍了下巴掌;“何处不宜春!是啊,山高挡不住春风来。贤弟远来山城,既来者,则安之,也莫负了春光啊!”
王勃骤然从诗情中醒觉,又慨然感叹:“唉,纵有豪情壮志,我这一介书生,寄情于山水之间,能有何作为!”
“道不同,不相为谋。”杜微劝慰道:“不立朝堂与狼狈为奸,能远至山野修身养性,不移壮志,著书立说。子安你德才兼备,智慧过人,何愁没有有道之君来访你于嘉陵江滨,早晚定有仁义王侯来三顾、四顾你书斋的。”
王勃摇摇头:“杜仁兄,你是替我在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呀!”说罢他将密函拿出,随手交给了杜微,独自沉默地面对群山。”
杜微阅信后,颇为庆幸地说:“哎呀呀,这信要落在高履行的手中,贤弟,你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王勃笑笑:“他可也是武后将他贬到此地来的呀!”
“那是因为他是长孙无忌夫人的兄弟,武则天妖后为排除异己下的毒手。长孙家族如今仅存的就剩下这个老不死的了。”杜微鄙视地介绍。
“他也够可怜的了!”王勃微有同情。
杜微气愤不平的说:“该可怜的是长孙家最后一株独根苗长孙铨。”
“你说的是金城公主的驸马爷。”
“这位当今皇上的亲妹夫,就是被高履行这位亲舅公密谋,让剑阁县令薛仁活活打死的。”杜微厌恶的说:“他呀就凭谋害亲外甥的心狠手辣,得到了妖后的欣赏,不单保住了自己狗命,现在他已升迁为益州长吏了。”
“那么,他究竟是子党的心腹,还是母党的亲信。”王勃追问细底。
“他是谁的心腹,谁的亲信,谁也不清楚。”
王勃讽刺道:“可以清楚的说谁向他扔肉骨头,他就效忠谁,去当谁的爪牙!”
“反正这类狗,为争肉骨头,人也咬,狗也咬!”
“是一条疯狗!哈哈哈”王勃大笑起来:“不要管狗咬狗了,走!”他跑下了关,翻身上马,挥鞭向前。
杜微随后追上去,二人双马并驰。
剑阁县山城景色,城依山而筑,山环城为屏。城外葛愦山腰古柏林畔,卢照邻,邵大震和一群慕王勃之名的年青文士,在树下,在岩上,翘首向远道眺望。
远远云雾袅袅的山谷中,隐隐可见王勃的一行人来了。
有人欢呼:“来了来了,王勃来了!……”
卢照邻一把握住邵大震的手臂,激动地说:“他来了,王勃平安地来了!”
“哎哟,哎哟……!”邵大震扒开卢照邻的手,幽默在抱怨:“王勃一路平安,我可无辜遭殃。”他抚着捏痛的手臂。
卢照邻又勾肩搭背地说:“你我互关痛痒,好朋友才让你悲欢共享啊!”
邵大震狠狠又刺一句:“哎呀呀,你要再流放,我也该受你诛连了。”
卢照邻小声地说:“有这个日月行空的武氏临朝专权,我俩这一对保皇死党啊,飞不了我,也逃不了你!哈哈哈哈……”他嚎放的大笑。
邵大震点着卢照邻鼻子,无言相斥,二人相视大笑,引得其他人转目注视。
“小心隔墙有耳!”邵大震止住笑容,拱了拱卢照邻,斜视了一下在另一大树旁的俊美青年。这青年似有察觉,神态不安。
“吐!”卢照邻啐了一口:“枉披了一张漂亮的人皮!”
邵大震胆怯地忙制止:“卢兄!……”
“哎呀,毒蛇!”卢照邻一声惊叫。
邵大震吓得慌忙躲闪:“在哪里?”
卢照邻挪挪嘴:“哪!”那青年忙退避大树后去了,他又嘲弄:“缩回去了!”
众文人哄然大笑,或明或暗注视着,并私议着那树后羞怯的青年。
并马而行的王勃问杜微:“大路上是些什么人?”
“前面那个大个子,象是剑阁卢县尉。”
“当今诗人卢照邻?”
杜微手打遮眼细看:“不错,正是卢大胡子。”
“哦卢照邻,卢照邻……”王勃激动高呼。他勒马加鞭冲向前去。
王勃疾驰到卢照邻身边,翻身跃下马来。卢照邻也奔跑过来。二人双双握住手臂急旋一圈,相互凝视,相对无语,相向痴笑……。
卢照邻这才觉得双臂酸痛:“你,你好大的力气。”
“你好大的胡子!”二人又畅怀而笑。
围观众人也随之大笑。
卢照邻揽着王勃向众人夸赞:“王勃王勃,果真是英气勃勃!”
“照邻啊照邻,看你如何照看近邻了。”杜微笑了过来。
卢照邻坦率地牢骚:“同是天涯宦游人,先后贬逐剑川来,我也是身陷泥潭,自身难保啊!”
王勃向憨儿:“憨儿拿过来。久闻卢兄诗名已贯遐迩,小弟相逢无以馈赠,特地敬录仁兄大作赠于仁兄。”他与憨儿展开横幅,他又朗诵道:“曲池荷花,此诗极佳,小弟为众位朗读,共同欣赏: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
卢兄啊,昔日你早已是浮香绕遍湖圹曲岸,圆叶覆盖过翠华碧池,何苦这样感叹唯恐秋风早呢?仁兄此身不沾污泥,纵然是红消香逝,翠叶不圆,你也在诗坛中硕果累累,结满莲子了啊!”
“哼哼,”卢照邻苦笑:“结果结果,结出的果果也是心中苦啊,今朝贤弟笔走龙蛇,这一手好字,使愚兄拙作增光生色,愧领了!”
杜微笑道:“子安贤弟挥毫赠墨宝,诗坛四杰你为首,众位雅士出城相迎,你也当赋新诗以酬卢兄旧作啊!”
众文人随声附和:“请诗友,请文豪即兴赋诗,以壮视听!”
王勃兴致很高:“恭敬不如从命,小弟也以荷花奉和卢兄一韵了:
凌波浴霞光,傲立无傍徨。
荷塘恋野趣,清凉品幽香。
众位学子拍手赞叹:“好诗,好诗。”
“好好好!”邵大震推了推卢照邻:“诗言志,瞧人家不慕杨花随风舞,甘于随世而安,自得其乐。你呀,不要总是抱怨一生飘零无人知,今朝知音欢聚,你又这样儿女情长,婆婆妈妈哪象个七尺男子,诗坛文豪。”
杜微笑道:“邵贤弟不愧雅号大震,一语就震得大胡子不敢胡说了。子安哪,这位就是卢兄的崇拜者,诗迷。是卢兄形影不离的影子,邵大震。”
王勃拱手施礼:“久闻大名,多多关照。”
邵大震指着周围的青年学子们:“我和他们才是久闻你的大名,如春雷贯耳,今后盼着你闭了门点灯,关照关照呢!”
众青年学子文士纷纷向王勃寒喧施礼,王勃诚惶诚恐,虔诚还礼。
那个俊美青年由大树后出来,欲进不进,欲语不语,他孤立于一块大石上张望,反而引起王勃的注视。
杜微悄悄向王勃提示:“他也是个‘人若其文’华而不实的吴子璋!”
卢照邻鄙视地补白:“貌若莲花者,本不是莲花,出污泥岂能不染。”
王勃眉心微蹙:“他……。”
杜微又补充:“也是我们的同僚。”
“同僚,同僚,话不投机半句多,无话可聊就不聊。”卢照邻粗声大气,公开用话刺人,又不拘小节拖着王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能合群的准定不识南北……”“更不是东西!”邵大震故意挑明歇后语。
“我们这群志同道合的,随我来。”卢照邻兴致更高。
邵大震来劲了:“酒逢知己千杯少。以文会友以酒助兴,走走,先来个一醉方休。”
卢照邻携着王勃走往古柏林,众人欢欣相随,欢声笑语风中飘扬。
那青年薛华无形中被单人撇下,孤零零地望着柏树林中,席地而坐,欢饮的人群,他懊伤,寂寥,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薛华进入剑阁县书斋,闷闷不乐脱下外衣随手一扔,外衣落在地下,他躺倒摇椅上,俊目中泪光闪闪,摇摇晃晃……。
县令夫人刘氏走了进来:“华儿,你又没能参加王勃他们的诗文聚会呀?这是第几次啦,你得主动去迎合,往他们里面挤呀!”她见薛华侧过脸去拭泪:“怎么,他们欺负你了?谁呀?”
薛华躺着顶撞:“我是县太爷的侄少爷,谁敢欺负我!”
刘氏坐拢去说:“不是叔叔婶婶逼你,这是高履行你那个干爹……”
薛华站了起来:“干爹干爹,什么干爹,老狐狸!”
“你!……”刘氏按耐下性来向书僮吩咐:“抱琴,守在外面,不要让人进来。”
薛华厌恶、冷漠,背过身去,刘氏一付委屈神态:“人家都以为你叔叔手毒心狠,活活打死了长孙铨驸马。其实那用刑的人,都是高履行派来的。这事你最清楚,没有你亲爹亲自来传高履行的指令,并带那两个刑讯逼供的衙役,哪能在公堂上就活活打死了人。”
“不要说了,你们搞得我也跟着揹骂名!”
“你叔叔才是个替高履行揹骂名的。不是他一手策画,你那夜路也不敢走的叔叔,有那包天胆吗?”
薛华沉默无语,低下了头坐到书桌前。
刘氏跟过去说:“我们也知道高履行是条老狐狸。可他是个通天人物啊!武后娘娘明明有懿旨先来要保住长孙铨驸马的性命,可他偏下这毒手害死亲外甥。山高皇帝远,他一面推说武皇后旨意来迟了。他竟又以此作为大义灭亲的壮举来向武后表忠、邀功,武皇后为这事将他提升了益州长吏,他又四处造谣,说这是武后娘娘灭人伦,无亲情。回过头来他,又以这事向长孙无忌和皇太子表了忠。”
“这个两面三刀的笑面虎,他那满肚子脏水别说了,我恶心。”
刘氏牛不饮水她强按头:“恶心也要听,话说回来。若是长孙驸马不死,你亲爹能高升为益州司马?你叔叔能连任剑阁县令?就凭你能做几篇诗赋,能让你来当县衙的主簿?”
“姨母,你不要说了?”薛华内疚地乞求。
“不!”刘氏硬着心肠又说:“你应该明白,高履行为什么逼着你认他为义父!”
“什么义子、义父!”薛华推开刘氏:“我们都成了不义的人了!”
“哎呀,我的小爷爷,你饶了我吧!”县令薛仁从门外冲了进来:“你这样大吵大叫还了得!”
刘氏拖开薛仁:“有什么了不得!看你这老鼠胆。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嘛!”
薛仁急了:“他不懂事,就更能坏我的大事!”
“怕坏你大事,又要他办事。他不懂其中的厉害,你不会调教他,我来开导他。”
薛华想避了出去。被刘氏拦了回来:“华儿。你妈是我亲姐姐,你爹是他亲哥哥,我们无儿无女,抱你回来抚育你这么大,还能将你往火坑里推呀!”
薛仁也接茬道:“你现在的这份差事,也是你义父高履行指明要你干的。”
薛华反感地:“我干不了!”
“不干也得干,王勃是武后娘娘亲自派人护送来的。”刘氏斩订截铁地命令。
薛仁说明实情:“皇太子殿下,也暗中几次让人来查问过王勃行迹了。”
刘氏说另一面:“武后又来过密旨,要我们不要干涉王勃的行为,还要保证他平安。”
薛仁接着说:“你义父要你一定与他搞得火火热热。”
刘氏:“死死盯牢他的人来客往,言行举动。”
薛仁耽忧说:“出了点差错,你义父要拿我是问的!”
刘氏更露骨:“这可关系到我一家子荣华富贵兴盛败落的身价性命啊!……”
薛华一语不发,瘫软在摇椅上任其摇晃。
卢照邻醉醺醺的由邵大震和王勃扶着进入衙门,走入后衙西套院幕僚们的住处,在院内桂花树下将卢照邻扶坐在竹躺椅上。
卢照邻推开他俩,醉言醉语:“……世人皆醉我独醒,醉酒,我只醉眼皮不醉心,睁开醉眼看闹市,满街都是纸醉金迷的糊涂人……”他扒在椅扶手上微微打呼噜。
邵大震叹气道:“你这个老光棍,该续个弦了,免得你天天以酒当茶喝……”
卢照邻喃喃对答:“我不……不要绍兴……女儿红……我要……山东的二窝头……”
邵大震笑道:“那你就让胭脂井茶馆的金寡妇招进门去好了!”
卢照邻打着呼说:“……真寡妇!……真寡妇好会疼人!……”
王勃笑道:“我以为卢兄是个海量呢!”
杜微也笑道:“他呀吃半碗糊子酒汤圆,也是昏昏沉沉说醉话。”
邵大震接着讽刺:“一口气再喝上二斤半烧酒,他也不会摸错了房门。”
王勃向自己房门喊道:“憨儿,泡壶酽茶来给卢大爷醒醒酒。”说罢又向杜、邵二人道:“我来衙内很久了,你们天天有公事忙来忙去,就剩下我一个人守在卧室里,陪着枕头伴着书,我闲得慌,更闷得慌,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卢照邻闭着眼睛插话:“……见怪不怪,就成了罗卜白菜……。”
“罗卜白菜……?”王勃笑道:“他这是什么酒话?”
“不,他不是九话是实话,少见多怪,多见了,不就成了见惯了的罗卜白菜。”邵大震解释。
“他这实话,实实在在是得道的半仙说偈语,不只是实话,而且是真言。”杜微推崇地说。
“看来我和卢兄交往,还少不了请二位给我当通司,作翻译,加注解。哈哈哈”他又向房内喊:“憨儿,酽茶快泡来呀!”他又再向杜邵二人说:“至今我还没有见着顶头上司,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卢照邻翻了个身自言:“就学那瞎子赶夜路,反正看不见……”
邵大震向王勃笑笑说:“他要你不紧不慢走着瞧,瞧也无用。”
杜微也笑道:“急也没有用!”
“憨儿!”他又喊,室内没动静。王勃向二人笑道:“大概我身上的瞌睡虫,都爬到他身上去了。说罢他进入房内,立刻又跑出来大喊:“憨儿,憨儿—!”
杜微问道:“出了什么事?”
王勃疑惑:“憨儿不见了,我室内的衣物书籍也不见了。难道说有人入室偷盗了。”
“哈哈哈”薛仁走进庭院:“哪个江洋大盗青天白日敢入县衙内院行窃。是本县命人将王少府的用物搬入后花园了。”
卢照邻侧过身去说酒话:“……不告而取总是偷偷!”
薛仁不介意地一笑:“嘿嘿,这个酒罐子又装多了,王少府恕我对下属不拘小节。”
杜微和邵大震上前行礼:“见过薛大人。”
“哈哈,你们是文人相交酒为媒,推杯换盏才有诗文。我啊只通些官样文章,就缺少你们这样的闲情雅致。真羡慕你们这些青年人啊!”
王勃上前施礼:“学生见过县台大人。”
薛仁上前扶住:“免礼免礼,不敢当不敢当。本县近有小恙,未能来访王少府,还望见谅。”
王勃恭谦地说:“敝人是县台属下,怎当得起大人过问,还望早日分派事务,让学生能够尽职尽力。”
“嗨,瘦了的骆驼比马壮。您是武皇后慧眼青睐的才子,皇太子器重的文杰。益州长吏高大人早已明示,武后娘娘旨意,让王少府暂且屈居衙内,调养身心,一旦朝中需要,将召你返回京都委以重任。”
王勃疑问道:“武皇后哪能下这样的懿旨?”
薛仁笑道:“总之这是上司指令,本县奉命执行。请!”他一付奉迎媚态的礼让,全无半点上司的架式。
王勃很不自在尴尬地问:“去哪里!”
薛仁恭请道:“凤栖梧桐,龙潜碧潭。请王少府迂居后花园清静的高处,鸣翠阁。”
县令薛仁和杜微陪着王勃来到鸣翠阁前。
薛仁十分客气:“尊驾能屈居小县,使这衙内蓬荜增光辉,全县添异彩。”王勃频频蹙眉,薛仁依然讨好:“这阁,后有古松,前载绿竹,每当清风徐来松涛高呼,翠竹低鸣,因之隋朝一位雅士题名曰鸣翠阁,是衙内最精致的所在,愿王少府在此多有佳作问世。”
鸣翠阁下,薛华正开门出来,不料与王勃照面,他又缩了进去,将门关上。
薛仁忙喊住:“华儿,出来。”
门又开了,薛华无奈何走了出来,沉默地站在门口。
薛仁热情介绍:“他叫薛华,是本县主簿,我的嫡亲侄儿。我特地命他住在这阁下面,与王少府作个伴。他呀,从小喜好诗赋。华儿,今后要向王少府多多讨教。”
薛华尊敬的深深拱手抓搑,王勃目不正视微微还礼,爱理不理地随即登楼走上阁去。
阁内憨儿正与书僮抱琴在整理书架、书桌。憨儿见了王勃,迎过来说:“公子,这里真清静。哦,他叫抱琴,是我的忘年之交。”
“忘年之交?”王勃乐了:“你也有了忘年之交。”
憨儿声明:“我比他大八岁,我和他已经是八拜之交,结拜的义兄弟了。我是他的干哥哥!”
王勃笑道:“好,你总算当上干哥哥,今后要互相关照,这一两银子,去给你干弟弟买件衣服,算我的贺礼。”
憨儿接过银子高兴地拉着抱琴:“走,我们逛大街去。”
他二人下楼正遇见薛华,抱琴欲言:“少爷!”
薛华笑了:“我知道,这里二两银是我的贺礼,你们哥儿俩去逛街吧!”
憨儿与抱琴携手雀跃而去。
杜微伴王勃在阁上围着环廊四下观望。鸣翠阁在县衙后花园的后方。阁后一道围墙依山而筑,从阁上看去,隔墙也是一座花园。园内有一股清泉曲曲流入一泓碧池中。只是那花园荒芜杂草丛生,花卉纷乱,一大片茂密的竹林,浓绿沉沉,给荒园更添了一种阴森森的气氛。
王勃似自言自语:“嗨,果然是吃人的老虎不露牙,这薛县令叔侄一俗一雅,看起来都文质彬彬的。杜兄,长孙驸马真正是被这个县太爷活活打死的。”
杜微怯怯地说:“我也是贬到剑阁才听人说的。唉!这里是个变相的监狱呀!”
王勃笑道:“我们都见过了,与朝堂相比还是这个监狱来得幽雅清静。”
杜微轻轻地说:“有人说剑阁县衙就是阎王殿,冤死的人不少啊!”
王勃坦然地:“京都更是个枉死城,昏君只要昏一昏头,全国冤死屈煞的人,阎王爷也计算不清!”
“小心!”杜微吓坏了:“你还是那个大嗓门,须防隔墙有耳。”指指阁下。
阁下仰慕王勃的薛华,无意听见,为避嫌退回到室内。
王勃笑道:“你也还是那样胆小怕事。一死无大难,怕什么?”
杜微笑了:“你光棍一条死了没有人哭,我可还有妻儿老小啊!”
王勃同意了:“是啊,人生难免一死,怕的就是钝刀子割肉,活罪难受啊!”
薛华在楼下,不自禁叹了口气;“唉!”他又自觉地立刻躲回房中,关上门。
“楼下有人!”王勃警惕地。
杜微提醒:“别忘了阎王离不开森罗殿,人间处处藏小鬼呀!”
阁上红烛高烧,一阵哄笑声中王勃手拿书卷指着经典驳经典,卢照邻拍案辩斥,粗声大气吼不停,杜微轻描淡写谈高论,邵大震痛心疾首吐妙言。憨儿和抱琴为他们上点心,筛热茶。四个人各抒己见谈笑生风。
卢照邻笑骂道:“我若是秦始皇,先将王勃的诗赋怪论全烧了,然后将你们三个大逆不道敢批经忘典的文人全活埋了!”
王勃笑道:“你呀焚书坑儒不管用了,如今争鸣何止百家,我们更是些已经不怕死,敢于骂阎罗的人。”
邵大震笑道:“屎坷郎莫要笑臭虫,我们都把屈原的文章当饭撑饱了,吐出来的不是离骚是牢骚。”
杜微提醒说“对对,不要在子安贤弟的鸣翠阁上,百家争鸣纸上谈兵了。”
卢照邻自我讪笑道:“是啊,秀才造反没有兵权,只能是胡扯蛋!”
邵大震笑道:“这里是品茶,不是酒,你呀不要借茶装醉又胡说八道了。”
杜微调停道:“诸位都是沦落人,牢骚可发不可吼。已经夜深人静了。”指指楼下:“人不怕吵,鬼怕吵;不要扰得鬼不安宁抱怨人啊!”
楼下薛华拥被而坐,闻楼上谈话,对孤灯蹙眉,辗转不安,起身在室内徘徊踱步。
邵大震故意危言耸听:“……听说这花园里不洁静,常有鬼魅孤仙出没。”
窗外传来远远狗吠,更夫敲更,一阵风吹得室内烛火摇曳。
卢照邻也作谈鬼色变:“瞧瞧深更半夜,秋风飒飒,这月黑风高多暗鬼,子安哪,你孤身只影,在这望乡阁上,不要人鬼不分,被鬼迷了心窍啊!”
王勃笑道:“有道是邪不压正,你醉话里说过多遍,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真有鬼,我到真想见活鬼呢。”
卢照邻也笑了:“你真的不怕鬼?”
“怕鬼?”王勃傲然笑道:“我敢鬼打架,他打死我,我也成了鬼;我把鬼揍死了,鬼变不成人,连鬼也做不了。”
憨儿和抱琴喊了进来:“宵夜来了!”
憨儿提着食盒:“炒米糖开水。”
抱琴也提起食盒:“糊子酒汤圆。”
卢照邻高兴地说:“好好,正对我味口。”
邵大震玩笑地:“不好,不好,正对你味口的,在胭脂河畔的茶馆里。”
王勃不解:“我的通司,这是句么事歇后语。”
杜微笑道:“卢大胡子最对味口的是茶馆里的金寡妇。”
邵大震再补充:“那是个俏寡妇,真寡妇,她是胡子,酒里的汤圆,味道好极了,是不是?”
楼上幽默豪放,嘻笑谩骂的谈论,使得在阁下室内徘徊的薛华脸上,羡慕地也展现出和善甜美的笑容。一阵楼梯响,薛华从门缝向外窥视,目送卢照邻一伙人去远了,他悄悄开门出来。
一钩缺月挂树梢,夜凉如水,梧桐树剪影上洒满银辉。薛华向鸣翠阁上望去,阁上王勃灯下书写,文思如潮,挥笔不停。
阁下,薛华卧在床上,彻夜不寐,长吁短叹,辗转难眠。他坐了起来也挑灯夜读以谴烦闷。
说书人缓缓评说:“挠不着的才是痒,说不出的才是苦。王勃是苦中作乐,有苦,知心朋友互相诉说,痛快!薛华是有苦难诉,忧郁只能伴孤灯,烦闷!鸣翠阁中秋夜长,长夜不眠,面对苦难,情境一样,心绪两样。同是纯正青年,同住一座阁中,今后遭遇会怎样?前途难料,人生路比秋夜长。茫茫、茫茫、路茫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