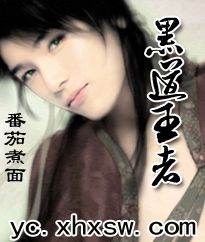正文 -- 第十二集人抬人高成奇货
第十二集人抬人高成奇货
说书人:人生若是大舞台。除了呱呱坠地时,清清白白赤裸裸地大喊大叫,无丝毫羞耻的心,怯畏的胆。一知人事,就得粉墨登场了,随世就俗,不得不各演各的戏,各唱各的调。为了识时务,谁也免不了因地而异,扮演生旦净末丑、忠奸刁恶贤的角色。人人都难以自赞自夸,自责自贬,自评自说。都得以别人说的,大伙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评估。做人难,难就难在这人生舞台上必须唱给别人听,演给别人看。好像就为演戏而活着,为别人而活着。王勃想随心所欲,不为取悦他人而活着。这样能行吗?他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
说书人音内的画映出:
吴子璋一走,王勃立刻跃下长榻,像顽童扒在窗上向外张望,只见兄长王勉殷勤相送,吴子璋边走边言明利害,反复叮嘱,王勉唯唯喏喏言听是从。
王勃在室内伸臂涮腰,提腿自旋,如释重负,无比轻松。
王勉送走吴子璋,王劬迎上前去询问情况。王勉忧心忡忡一一相告,王劬听之叹之不住摇首。兄弟二人进入王福畤卧室,如实禀告。父子三人商议对策。
王勃舒筋活血轻微活动后,又拿起“易经”正襟危坐阅读,王劬、王勉随着忧愤不安的王福畤闯进书斋。
王勃立刻起身,持书躬迎:“父亲……”
王福畤不作答理,直径走到长榻前转身又怨又恨,气恼难忍,无言以对地怒盯着王勃。
王勃查觉父亲的不满,佯着木讷:“父亲……”
王福畤站立着问:“你,你病了,什么病?”
王勃皮笑肉不笑地说:“孩儿我………是权宜之计。”
王福畤愤恨地说:“你一惯以坦直豪爽,光明磊落自居,而今也诡计多端的捉弄人了!”
王勉劝导地:“那吴子璋待你不薄啊。”
王劬指责地相劝:“你能说他这样热情前来,藏有什么鬼心肠。”
王勃认错地辩解:“我知道吴子璋真诚待我,他想帮助我找个庇护的大树。”
王勉急忙赞同:“背靠上了大树能避风雨呀。”
“经受过风雨,我才能独自抗风雨!”
王劬指要害:“皇亲国戚只能奉承,必须应酬,千万不能得罪呀!”
王勃不满地说:“难道逢场就得作戏,一切都要演给别人看,你们不觉得这样做人太辛苦了吗?”
王勉劝说:“辛苦也得礼上往来装笑脸。”
王劬再指明原因:“纪王是皇太子的岳祖父,不言而喻,他是东宫太子一党的呀!”
“难道武皇后又是一党”王勃见他们三人颔首默认,他又问:“你们是子党,还是母党?”
“这……。”三人都难明言,只有王福畤阐明立场道:“他们结党都是营私。我家忠于天子,辅保社稷,两方面都不能偏颇,不能参与。”
王勉王劬异口同语:“更不能得罪。”
王勃不知轻重,依然调侃:“你们想脚踏两条船吧?”
王福畤为王勃稚气焦燥,又训斥了:“我是要你,哪一条船不要踏上去。”
王勃不以为然,坦然言之:“母党子党,而今忽暗忽明都在耍弄权谋,都能左右朝政。立于朝堂的官宦,无人不知他们双方的明争暗斗。在这势均力敌,势倾朝野,势不两立的形势中,不靠向哪一党,能在中间立得正,站得稳吗?”王勃故意挑逗,再加一句:“我若不明真象,有了偏向呢?”
王福畤难以回答,两个长子也哑口无言,他只能恼火地呵责:“那,那你是该死!”
王勃竟轻松幽默地微笑自嘲:“嘿嘿,看来我是该死,迟早是死定了!”
王福畤气恼地起身,走到门口转身命令地:“王勉,明日你备上一份厚礼送往纪王府去。王勃,你必须用心写一祝寿条幅前去贺寿!”
王勃还想讨价还价:“父亲……。”
“你若不写,从此莫来见我!”王福畤扔下这句话愤然而去。
王勃无可奈何,长叹一声泄气地坐在桌前。
鸟瞰纪王府。喜乐声中,府前车水马龙,府内彩棚高架,由外而内人流不断,张灯结彩全然一派寿诞喜气。
女嫔客流散入了府内花园亭台楼阁中。皇太子的纪贵妃陪伴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一群宫娥彩女引导下经假山曲径,花桥长廊来到品月阁。阁中高官贵胄的女眷,阁外跪迎。
在阁内四望厅中,众夫人小姐团团簇拥在太平公主周围,纪贵妃忙着捧茶,拿点心敬奉公主。公主如鱼得水,悠然自得,谈笑生风。
小喜鹊和奶妈伴扶着阎秀芹来到公主前面,秀芹下跪施礼:“公主在上,小女子阎门秀芹,愿公主千岁,千千岁!”
“婉儿快扶她起来。今日大家都来为阁老纪王爷古稀高龄祝寿,小姑娘怎么祝愿我千岁,千千岁起来。我若真是千岁了,我这千岁老太婆。可嫉妒死你们这些千娇百媚的夫人小姐了。”太平公主一席话,逗得众女眷嘻笑雀噪一阵阵。
服饰淡雅,淡妆素抹的秀芹,在阁上穿红着绿裙衫华贵,珠光宝气的女嫔中,更显得高雅夺目如鹤立鸡群。婉儿喜爱地特地牵她到太平公主面前。太平公主这才引起注目,情不自禁地惊叹:“嗨,这样一位窈窕淑女,婉儿,你说说是我美,还是她漂亮?”
婉儿故作左看右瞧反复比较:“我看,她比你美,你比她漂亮。纪贵妃你说是不是。”
“去你的,废话,说了白说。”
纪贵妃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罢,我到前厅去请些君子来鉴赏鉴赏,评判评判。”
众女宾又是一阵哄笑。
太平公主还在打量着秀芹笑向众人:“我看她芙蓉出水,清香淡雅美在自然。”
“怎比得公主是盛开牡丹,端庄浓艳国色天香。”婉儿接着夸公主。
公主拉着秀芹的手嗔斥道:“她这丫头就会吹捧奉承。”
婉儿辩护道:“不信的话,奴婢就去将那个为公主题‘牡丹颂’的风流才子吴子璋请来。”
纪贵妃见公主笑而不语:“要不,连同誉满京师的奇才王勃,也一同请上阁来。”
众眷属笑着起哄:“好啊,好啊……!”
公主笑向众人:“得得,你们都是名花有主的贵妃,夫人,我们可是些含苞未放的公主小姐,按礼教男女有别,岂能容那些狂峰浪蝶来扰了我们的清静。纪贵妃,哪个王勃已经来了吗?”
纪贵妃:“听你大哥李弘,和我爷爷老寿星说,这样的盛宴,他准会来与吴子璋题诗作赋斗文彩的。”
公主说道:“我今天要仔细看看王勃这个倔犟的牛犊,能不能胜过吴子璋。”
“一定能胜过吴子璋!”小喜鹊情不自禁插嘴:
“不许胡说!”秀芹轻轻斥责。
“是你自己说的嘛!”小喜鹊低头咕噜。
公主笑了:“你也是来看王勃的?”她见秀芹默默无语,又微微摇头:“瞧你这羞人答答的模样,真叫人不能不疼爱。嫂子,她是谁家的闺阁千金?啊!”
纪贵妃道:“她就是统领京都九门龙武大将军,阎伯屿的掌上明珠阎秀芹。”
婉儿问道:“你就是那个京都师从大画师阎立本能书善画的才女?”
秀芹歉身答:阎公仍是本家叔公,家父随太宗西征时,奴家寄居在他府中,承他宠爱,从小受他传授学涂鸦,不敢称得能书善画,小女子实实无才。”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不是?”太平公主调笑道:“别听那些迂腐蠢夫的女儿经。女儿家能断文识字,明经据典,才能通晓礼法。我母后德高望重,就是因为有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之才,才能在我父王久病体衰,难以临朝之际,除奸佞,举贤能,替天牧民,辅助皇上治理得国泰民安,万邦来朝。女人有才照样能臣服朝野的文臣武将,贤士能人。女人无才那是缺德。德才德才,没有才,不懂道理,还谈什么贤德。秀芹,你说本公主说得在理不在理?”
秀芹十分敬佩,顿成知音:“听公主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家父有很多迂腐礼教,与奴家深究的老庄之道大相径庭,因矛盾而争执。家父总是呵责道:‘女子无才就是德’说我秀芹书读多了。”
“哈哈哈”太平公主笑道:“阎伯屿这类武夫,和纪王爷一样。自己不明经史,不知诗书难以达理。他们在朝堂上无理说服我母后的治国方略。背后抱怨的也都是这句说:(学武将口气)皇后娘娘若是无才少读书,哪能有这样多气吞山河的大政方略来垂廉听政,扰得我们文臣有口难张,武臣晕头转向。”
秀芹初次听得这样大胆评议朝臣的言论,颇为惊异,非常感兴趣,立刻问:“为什么”?
太平公主来劲了:“我母后有才,才有真知灼见讲治国的道义,安邦德行。使文臣再无其他经天纬地的歪理可辩,只能张口无言。那些只擅长盘马弯弓、挥刀弄枪少读书,无知识的武将,听了这些高谈阔论定国安邦的玄妙大法,他们如同吃蜡。不知其三味,怎能不七晕八素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婉儿提醒的:“公主,今日是战功卓绝老将军纪王爷的寿诞,您不要信口开河,进入寺庙笑秃头了。”
纪贵妃笑道:“我祖父和秀芹的父亲,他们自己早已感到,读书太少,就悟不透孙子兵法的计谋,而今他们最敬重的是饱学长老。来往最多的也是些文人雅士了。”
太平公主也笑道:“但愿我们这两位老而开明的虎将,是悟了真理的朝外居士,千万别是秃子挤进寺院,冒充真和尚。”
公主的说话,人贵话也重,女眷们无人指责却都牵强附会的随之嘻笑。
这时有人喊道:“快来看那!摔跤开始了。”
太平公主和女眷们在阁外回廊上观看。
东宫的摔跤手与英王府的摔跤手在图腾的旗帜引导下入扬,两队彪捍的摔跤手,相对跳跃跨步,互展威武。
看台的彩棚下,纪王和阎伯屿相坐一处。皇太子李弘、沛王李贤、英王李显和尚在少年的殷王李旦和傻子梁王、李忠列坐上席,英王和皇太子席前更摆了赏赐的金银元宝。
东宫的摔跤手动作敏捷,功力很深,接连两三个英王府的摔跤手被迅速摔倒,败退下阵。李弘每次胜利,都扔给得胜的摔跤手一只金元宝。英王李显连连派出的摔跤手,垂头丧气地退回队列。最后他气得满脸大红:’都是废物。来呀,将他们拉去各抽二十皮鞭!”
英王随从一拥而上架走了三个斗败的摔跤手。
品月阁上。太平公主向婉儿:“这哪里是摔跤比武激励斗志。分明是皇家子弟在斗气。”她拉着秀芹:“不看这个。我们聊天去。”
公主领着秀芹、上官婉儿和纪贵妃进入阁内。
看台上。沛王李贤向英王李显道:“三弟,你花了那么多精力,就圈养着这样一批丢人现眼的癞蛤蟆呀。”
殷王李旦拍手梁王李忠也随着嘲笑:“癞哈蟆,呱呱呱,三哥牵来当骏马,上阵摔了个四脚爬。”
李弘饮酒笑道:“火王爷,你还是将这三只田鸡,让你那养鸡的小肥猪再驯养驯养吧!”
喝着闷酒的英王李显,扔了玉盏,冲到东宫摔跤手前,脱了身上的袍服,扔得远远的。拉出了那个连连得胜的摔跤手,吼道:“来,你的功夫高深,来与我英王摔一摔!”
李旦拍手助威:“三哥出了马,一个能抵俩!”
李弘向自己的摔跤手挤挤眼:“你陪英王爷玩一玩。”
“不是玩,是摔。你摔倒了英王我,重重有赏!”
东宫摔跤手行过大礼,摆开架势。
英王冲过去,迅速地将他摔倒了。众人鼓掌。英王洋洋得意,四下环视。
一个纪府内侍过来向纪王禀报了什么,纪王约了阎伯屿匆匆离去。
东宫摔跤手懒懒地爬了起来。还没有站定。英王又冲过去,将他摔了个仰天翻。众人喝彩声更高。英王更不可一世地跃武扬威,殷王李旦捧酒送过去,英王双手接过,左右开弓一口一杯饮尽,扔了酒杯,他见那率跤手坐在地上稍歇,站起来掸掸土。李显再次冲上去,一个大大的“背包袱”,再次将摔跤手摔了个“硬抢背”。这一摔,摔得那摔跤手红了眼,他一跃而起,冲到英王身边吼了声:“我和你真正的摔!”他一个回合将英王摔倒地上。众人“哦!”的一声,煞时一阵寂静。摔跤手冷冷地僵立着,等着可怕的命运。
李弘紧蹙双眉愠怒地:“拉下去重责一百皮鞭!”
东宫卫士拥上前,架住了摔跤手。
“站住!”英王从地上爬起来,冲到摔跤手面前,狠狠几个耳光。
“三弟……”李弘过来赔礼。
英王涨红了脸,把李弘推开,冲到桌前捧起一盆赏银,又冲到东宫摔手面前,塞到他怀内。摔跤手捧过赏银跪下:“谢英王殿下。”
英王一挥手带着自己随从,不辞而别,匆匆离去。
李弘淡淡一笑,回过身来:“大胆,竟敢违抗我旨意,免责一百,敲……他个五十!”又在摔跤手头子轻轻敲了敲,又会意笑了笑。
摔跤手捧着满满的一盘赏银,昂头挺胸得意地被押走了。
李贤牵着四弟李旦过来:“大哥,你看三弟……”。
李弘摇了摇头:“火王爷就是这么个炸药脾气,现在别去招惹他。等一阵他那火气就散了。”他抚着李旦头说:“小四,和他们去打马球吧!”
几个随从跟着李旦走了。
李弘向李贤道:“二圣贤,你现在道行高了嘛,略略耍了点小计谋,就将刘祥道那个糟老头捉弄得闷声不出气,还把王勃那个眼线、耳报神拒在门外,你比他神童还神呢!”
李贤笑笑:“我这些还不全仗皇太子殿下高明的指点。不露声,不显迹,连母后都没有出面干涉,斥责我抗旨不遵呢。”
李弘问:“刚才两位老将军急匆匆走了,好象前面出了什么事?”
李贤:“那个家将小声来禀报说王勃生病不能来祝寿,送来一个什么,没听清楚……”
李弘道:“咱俩去瞧瞧。……王勃是母后新相中的一个棋子,他虽不像李义府,许敬宗是她清除朝中异己的车马炮,可是王勃也是个过了河,只进不退,敢于横冲直闯的过河卒。母后已将他投放到我们皇家禁地中来了。”他们边走边谈。
李贤又上套了:“什么过河卒,分明是个丧门星。不知道该我们兄弟谁倒霉,要栽在他手中。”
“放心,他手长就剁他的手。”李弘进一步施计谋了:“二弟,王勃虽被你拒之门外,但名份已册封是你沛王府的陪读舍人……。”
“大哥,你看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李弘像是十分关怀:“二弟你太厚道,只要你关紧府门,不放进这狡猾的狐狸。大哥会布下陷井,诱他落网。你就安心在府中去调教你的鹰犬走马吧!”
李贤心悦诚服:“大哥不愧有帝王胸怀,还真有先祖太宗料事如神的遗风。”
李弘李贤亲兄弟,貌似亲如手足,又各怀鬼胎心照不宣地走在纪王府的花径长廊中。
纪王府花厅中,刚刚正挂出王勃差憨儿送来的条屏,众文武宾客被展示的字画惊愕得口张目呆鸦雀无声。条屏右上端隐隐可见远远的淡墨青山,飘逸在浮云之上,一个粗壮端正有力用朱砂写的棣书红色大福字,福字右上角浓墨挥洒写了个一笔挥就的狂草寿字,在红福相比下寿字显得很短。
纪王气恼地吼道:“大家看看,今日老夫七十华诞,王勃托病不能来祝贺,我不怪罪于他,可他竟差这个憨头小子,送来这个亲笔书写的条屏来羞辱老夫。伯屿你说说这寿屏嘲讽的恶意!”
阎伯屿无奈猜释道:“这……红福太大,寿必短……”
“可恼!”皇太子李弘冲入厅正中:“这小子竟敢渺视随先祖太宗西征,血战沙场,开疆拓土的建国元勋,本王我的岳祖公,如此恶意犯上,哪能宽容,来呀!”
吓坏了的憨儿急忙上前,指着吴子璋:“不不,这个条幅是我家少公子按吴学士意图写的。吴学士这是我家公子命奴才亲手交给你的书信。”他将信交给藏在人后的吴子璋。
吴子璋在众目睽睽打开王勃带来的信函。他看后脸色由忧转喜,转向纪王道:“哈嘿,朝散郎王勃确是有病,学生昨日邀他今朝同来向纪王爷贺寿,当时合意写一幅祝寿条屏,他的已经完成,下一半落款题诗将由我当众献丑了。请拿笔墨来。”
侍从拿来笔墨,吴子璋环视众人,面带微笑略略拱手施礼,然后欣然提笔,饱蘸浓墨行蛇走龙扬扬洒洒在条幅留有的题款上写下一首贺寿诗:
纪王功高似南山,
鸿福横来寿嫌短。
难超彭祖活千岁,
定越古稀过百年。
阎伯屿颇感兴趣地朗读了此诗并赞道:“好诗,好字,好文采,这王勃和吴子璋可谓难得的才华。纪王爷,他们赞你功高有鸿福,七十不属高龄,年过了百岁才去比南山呢。”
“这些年轻人那……哈哈哈”纪王爷乐了。“看赏”!
憨儿傻赫赫地捧元宝而去。
这时众人也随之而笑,称赞连声。
杜微匆匆进来,向阎伯屿悄悄禀报了什么,阎伯屿又向纪王轻声相告。二位老将军匆匆离开了大厅。顿时厅内众目关注,雀噪声渐轻,众人纷纷猜测议论。
太子李弘吩咐亲随曹达:“你快去……”
曹达领悟地,悄悄随二老而去
品月阁上。众女眷正陪着公主谈笑。
太平公主正笑着向秀芹和婉儿道:“这个王勃啊总是满腹经纶,独出奇才,勿现勿隐不露青山真面目。”
婉儿笑道:“那个吴子璋就爱逢场作戏,哗众取宠,博取喝彩不让人。”
秀芹真诚地说:“人生最难才高八斗全是真学问,唯愿他俩才学相当,不相轻视”。
太平公主嘲笑道:“男人个个争强好胜,瞧我那几个皇兄,个个都相互逞能不相让。”
婉儿印证着:“一个竹篱笆围子里,圈不住两只叫鸡公。”
纪王妃道:“怎么女人在一起,总爱谈男人。”
婉儿调笑道:“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公主乐了:“对,掌握了男人的弱点,才能改变妻随夫荣,也让他们男人都能够妇叫夫随,一喊就到!”
众女眷们哄地大笑。
秀芹的奶妈急匆匆走到她身边惊张失态悄悄地说:“杜学士带来消息,我家望远少爷在高句丽牺牲了。”
公主询问:“谁来送信,谁牺牲了?”
秀芹强作镇静:“聚贤殿杜微学士带来消息我堂兄阎望远在东征中……为国……捐躯了……”秀芹泣不成声。
奶妈:“老爷命我接小姐速速回府。”
秀芹向公主叩别,公主扶送秀芹至楼梯口,众人在阁上窗前,目送忍悲暗泣的秀芹隐入花木丛中。
李弘和裴炎在廊下,看着阎伯屿父女相扶离开纪王府,杜微随在他们身后,穿过迎面而立的宾客。宾客纷纷侧立两边,肃立以表哀思。
李弘向裴炎道:“你真不该将杜微这个胆小鬼,按插到聚贤殿北门学士中去。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裴炎道:“微臣原本想将那个不满东征,爱发牢骚的阎望远,调遣去东征做个异乡野鬼,没料他临死前,竟托人捎来封透露东征败绩,叫屈喊冤的遗书给他的知心好友。”
“你说杜微是那该死的知心好友?”李弘焦急地说:“这要让杜微这个祸害透露了军情,哪还了得。”
裴炎安然地说:“微臣特来找你,就是让殿下放宽心。杜微我已命人暗中将他控制,不容他与其他人往来,并宣扬他得罪了殿下,不久就要贬谪西蜀。”
李弘悬着的心放下了,以敬重作表扬:“老太傅果然足智多谋,纵擒自由,疏而不漏,本王自愧不如。”
“不不不!”裴炎以谦逊示忠心:“微臣谋略粗浅,怎及得殿下帝王胸怀,谴调千军万马,深藏神机妙算。老臣全仗殿下殷勤指点,才胸有城府少出了差错。”
曹达过来回禀:“已经查明,王勃并没有重病卧床不起,他是怕来拜寿遇见沛王和殿下您。”他又暗里中伤:“也不知吴子璋对他了说什么,王勃见我就推诿回避,像是心中有鬼。”
裴炎冷冷地说:“看来他是寄期望于皇后娘娘。”
李弘以小人心度王勃:“他想攀高枝一步登天?”
“非也。”裴炎向李弘让坐,二人坐在石桌两侧。他款款而谈:“马为策己者驰,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用。”
李弘有所悟:“哦,你认为王勃已视刘祥道为知己者,他也自甘投入我母后鸾驾前,愿为她勤于奔命?”
裴炎肯定地:“此言不差。骥马骙骙,桀骜不驯,是其本性。可是良马重义,不辨忠奸。”
曹达附和赞同:“再好的骏马也是畜牲,它眼里认定主子的好坏,就是多加给它草料。看来王勃是存心不肯投靠殿下。”
“好个不识抬举的畜牲。”李弘沉不住气了:“你差人去将他私下结果了。”
“不可!”裴炎立即阻止:“王勃如今是皇后娘娘格外器重的人才。更何况才高志大他正在择明主,现在还游疑未定应该投靠谁呢。”
李弘又有所悟:“嗯,王勃现在不愿当沛王的鹰犬,也还没成为母后忠实的走狗,是不能因小失大……。”
“殿下欲成大事,贵在选贤任能。”裴炎启示地说:“哪怕是鸡鸣狗盗之流,殿下也要学孟尝君收容府中。切不可让智士能人为对方所用。”
李弘:“这个奶臭未干的小子,能有多大才能!”
裴炎不得不言明利害:“他不仅受其祖父文中子和他师父颜师古的熏陶,有一定政见和抱负。而且写文章才思敏捷如有腹稿。”
曹达也补充:“对,写起文章来拂纸如飞,据说比吴子璋还快。”
李弘有点烦了:“吴子璋,吴子璋,你就巴不得有个人超过吴子璋!”
曹达自责似地辩解:“我,我又没有贬低吴学士。”
裴炎不理他俩经常性的斗嘴,故作声张吸引李弘:“嗨,近来王勃成了风云人物啦!”
李弘:“又有什么新闻了吗?”
裴炎接曹达语言:“不是新闻,也是新文,只要是他新写的文章诗赋问世,人们争相传抄。虽不能夸他的文笔如左思的‘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但他来京不久,名人雅士争着与他交往,邀他一同谈古论今,一同吟诗作赋。”曹达抢话道:“他如今人在京师,名声已扬海内了。”曹达有意表彰王勃。
李弘似信非信:“难道他的才思文章,真能压倒吴子璋?”
“文章各有所好,王勃文风全都是由感而发,言之有物,文笔洒脱不拘一格,畅所欲言不避嫌恶,胆大妄为敢于抗争。褒扬的说他文如其人,清新独特,有骨气;贬斥的讲,他人的如其文,粗野鲁莽,不高雅。”裴炎实事求是地讲。
“哈哈哈”李弘笑道:“他也像吴子璋,人如其文,文若其人啊!”
裴炎印证着:“雅士文人文风各异,书写的法家笔迹不同。正如殿下,龙行虎步非常人气度。”
“对对对。”曹达奉承:“白雪上的足迹,鸡绘竹叶,狗画梅花,再美也是小里小气,禽兽嘛!”
李弘呵斥:“你才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你懂得什么?不许多嘴。裴尚书,照你这样说,王勃在当今文坛,该独领风骚了?”
裴炎又道:“他初出茅芦,还是不畏虎的牛犊。但是个横空出世的扫帚星,尚不知给谁带来祸,给谁兆示福。当前确已醒人眼目,士人俗子已将他与户照邻、骆宾王、杨炯并称为当今文坛四杰了。”
曹达又在中伤:“瞧,四杰中就排不上吴子璋!”
“滚开!”曹达皮笑肉不笑,挤眉弄眼赖皮地退开。李弘四下略略思量后说:“王勃这狂生一向贬斥东征的丰功伟绩,如同我母后的喉舌。我岂能容他再成为我母后的刀笔。”
裴轻言重落:“殿下,争取此人誓在必得。千万不要未定胜负,就珠损玉碎,坏了殿下仁义厚道,礼贤下士的盛名。”
李弘开始急燥了:“我母后权高势大,点石能成金。我堂堂即将继位的皇太子,总不能容这个毛头小子,为我那谋权篡位的母后所用,让他在我眼皮底下恣意逞能,辉煌腾达吧!”
裴炎水到渠成语重心长地说:“殿下何不用他的文笔,来撰写九成宫前的记功碑文。这样,岂不是将皇后娘娘要纳为心腹的,变成……”
“变成了母后的心腹之患!”李弘顿开茅塞!“这样对王勃的去留、存亡,不用我吹灰之力了……,不,假若他不肯从命呢?”
“违抗王命,岂不正好——”裴炎以手比斩式。
李弘满面杀气,恶声恶气地吼道:“对,倔犟的烈马,不中骑就宰了它!”
裴炎立马制止:“殿下,这是纪王寿诞之期呀……”
二人同时左右打量,曹达望风示意指向远远而来的宾客。
李弘君臣顿作娓娓闲谈状态。
早朝后,朝臣们纷纷退出两仪殿,走出太极宫。裴炎追上王福畤将他拉向一侧:“王尚书,皇太子殿下口谕,让令郎王勃为九成宫的记功碑,撰写一篇吾皇东征高句丽丰功伟绩的碑文。”
王福畤顿感到棘手,马上推托:“京都人才济济,我那蠢才哪有这份才华。”
“你呀,又过谦了。”裴炎也客套地奉承:“太子殿下如此器重令郎,这可是他的鸿运高照啊!”说罢不等王福畤开口。拱拱手扬长而去。”
王福畤僵立宫外愁锁眉头,石压心上。
中书省刘祥道的署事厅内。
刘祥道拍案起立,问着苦着脸的王福畤:“好个脆计多端的裴炎,他们想一箭双雕!”他来回徘徊了一下,猛然停住:“嗯,我们也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对,就用他们的馒头,塞他们的口。”说罢他不自觉地为自己这高招笑了起来。
王福畤直愣愣望着嘻笑达观的刘祥道:“……什么馒头,去塞他们谁的口?……”
“馒头,还包子哟。我,嗨真有点对牛弹琴!”
王福畤有点生气:“我不懂!我是牛!可我哪能知道你这个馒头,算个什么计谋,又要针对谁了。”
刘祥道质问:“你没有发现裴炎这个老贼帮助皇太子在算计你家王勃?”
王福畤一愣,有点疑惑:“他们为什么要算计我家那犟小子?……就为撰写这篇记功碑文?”
“不为这碑文你来找我做什么?”
“我那倔犟的小子,我怕他写不好,也不肯写。”
“不不不!”刘祥道故意反驳:“你府上这位北斗魁星,才名已满京都,依他的才华,别说这篇碑文,再来个十篇八篇,他也不在话下。”
王福畤认真地解释:“老兄,我就怨你在武皇后面前呈上他那篇该死的谏言奏章。他一惯反对东征,怎能写得好为东征歌功颂德的碑文?再说他那宁折不屈,认死理的犟脾气,也决不肯委曲求全。”
刘祥道故意顶牛:“父命难违!王命更难违!”
“是啊是啊!”王福畤忧心忡忡:“他若坚决不写,这是执意犯上,违抗王命,是死罪呀。”
“如果他怕诛连全家,遵从你父命;你就不怕辜负武后娘娘对王勃的期望。”
“期望什么?”
“期望他刚直不阿,秉持正义,千万不要误投奸党,为虎作伥。”
王福畤求饶了:“皇后娘娘也是得罪不得的,所以我才来求老兄帮我拿过主意呀。”
“主意你自己拿!”刘祥道故意刁难:“儿子不肯写,老子替他写!”
“这样我不就与裴炎那奸贼同流合污了。”
“你既能说这句话,我才没有看错你,你还没有糊涂到甘心坠入奸党。”
“现在朝中谁忠谁奸,泾渭早已分明了嘛。”
“你呀,既能明辨是非,就不能明珠暗投,再骑墙了。”他指责了王福畤,又关切地说:“还呆着做什么?我马上去找太平公主,与她一同尽快将令郎送进沛王府,你呢,马上去找皇太子的宠臣吴子璋。”
“我去找吴子璋做什么?”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吴子璋春风得意,在文章上是不肯让人的。”刘祥道耐心启发。
“你的意思,让吴子璋来撰那碑文。他肯吗?”王福畤太忠厚老实。
“你呀,比起你那儿子来;他太聪明了一点,你也太蠢了一点!”他又耐心地与王福畤走出中书省署事厅,细细向他传授行动细节。
王福畤官邸。他回家正在院内向憨儿问话:“怎么,他没有留下话就出去了。”
憨儿答道:“五公子到灞桥给集贤殿杜学士送行去了。”
“这个蠢才,他明知道杜微得罪了皇太子殿下才贬谪到西蜀的,他……唉!”王福畤无奈感叹。
随在他身边的长子王勉:“五弟真是大智若愚,聪明得过了头,官场交往哪能动真情,他呀太讲义气了。”
王福畤向憨儿:“快去将五公子追回来。”憨儿匆匆去后,他向王勉:“你让你二弟去请吴子璋,怎么还没回来。”
王勉道:“瞧,吴子璋终于让二弟请来了。”
吴子璋走来深深施礼:“王尚书特地来邀学生过府,有何赐教?”
王福畤还礼道:“吴学士德高望重,文采超群学冠群英,下官礼部奉旨撰文,特请吴学士鼎立相助,请厅内小宴说话。”
王福畤施礼让路,吴子璋也向王家父子礼让。一番官样客套,王福畤与吴子璋并肩而行,王勉王劬随后跟着。
长安城外,曲江江水东流,垂柳柳丝随风,灞桥拱架似虹,郊外行人稀疏。一座凉亭中,杯盘狼藉,王勃在石桌上挥笔题诗。题罢将诗文送赠给贬谪川蜀的挚友杜微。
杜微深情地朗读,声音苍凉颇有伤感: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王勃走出亭外,步经垂柳边,他依古人习俗折柳,双手躬敬赠给杜微,接着激情昂扬高声朗读: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杜微紧握王勃双手,感激而又感慨叹道:“昔日初列金榜,平步青云,我是高朋满座,吟诗作赋争相唱和。真是青春相逢好结伴,大家都说有酒同醉,相知何必曾相识。怎奈命不由己,愚兄无意中未能投合权贵的意图,泄露了他们东征的机密,就这样一纸王命,将我贬至千里外,去那巴人蜀国蛮荒之地。今日若非贤弟前来相送。我只能是失群孤雁,独自飘零了。”
王勃劝慰道:“人生苦短,最苦莫过入宦海,十年寒窗博得一时荣耀,沐浴皇恩难料旦夕祸福。”
杜微:“贤弟初涉官场,哪知在这以命作赌注的生死场中,变幻莫测、冷热无常。伴君如伴虎古今是一样啊”。
王勃:“唯望仁兄远去西蜀,只当苦修悟道,如同庄周梦化蝴蝶,超脱了凡尘,寄身心于云水山川,岂不是悠然自得,乐如归去吗?”
杜微颇感宽慰,强作笑容:“听君一番指点,我一定铭记在胸,只当脱离了苦海抵彼岸。不像我的阎兄望远,被迫去东征,枉死在异国他乡,作了皇太子李弘谋权篡位的过河卒。”
王勃感叹地:“唉,命不由己身由己,你我定要凭良心,秉公仗义,尽可能为民造福,好自为之。”
“说是容易,做,实在难哪!”杜微临别吐衷肠:“子安哪,而今子党母党明争暗斗,各自都打着招贤纳士的晃子,实实都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密谋行奸。武皇后刁钻阴毒,太子李弘奸诈乖戾。他们双方都虎视眈眈,瞅着你,巴望你成为他们爪牙呢!”
王勃笑笑:“只怕我这颗顽石,可能崩掉他们的虎牙!哈哈哈……。”
憨儿匆匆跑来:“公子……。”欲言未语。
王勃疑问:“出了什么事?”
憨儿要说难说,又不会说谎,还是说了:“老爷说……老爷说,说杜学士是得罪了……”
“知道了,你回去吧!”王勃不让他说下去。
憨儿为爱护王勃发了憨劲:“不,老爷要你……”
杜微颇感不安:“贤弟不必久留,免得令尊担心。”
王勃胆壮气粗:“你我来往光明磊落,有何畏惧!”
杜微诚恳相告:“嗨,若让太子的耳目察觉,有碍贤弟前程!”
王勃握住杜微手腕:“走,我送你上船!”
“公子!”憨儿憨里憨气拦住王勃,被王勃气恼地推得踉跄后退。
王勃与杜微携手过了灞桥。刘祥道的差官急冲冲走来,打躬地拦住王勃:“王舍人,你让我们找得好苦。”他们都满脸堆笑。
“舍人!我算哪个王府的舍人?”王勃冷若冰霜。
“我们相爷差小人们请你同去沛王府。”
“王府门第太高,我高攀不上。”
王勃携住杜微扭头就走,差官们低声下气,尾随乞求:“王舍人……”
曹达领着几个东宫禁卫士,过了灞桥急冲冲包抄拦住了王勃去路。他笑容可掬如遇知己:“贤弟呀,快快,你福星高照,鸿运来了!”他一把抓住王勃,拖着就走。
王勃以手拂开,厌恶地:“你这白虎星不给我带来横祸,就是上大大吉了!”
“子安……”杜微担忧地将他往后拉着走。
曹达横插中间,分开了杜微,一脸媚态:“皇太子殿下久闻阁下大名,几次要与您会晤,没能如愿以偿。今日特命我来召见,去九成宫有要事相商。请!”他躬身让路。
差官拦上前:“曹公公,对不住,王舍人是沛王府的朝散郎,沛王爷的陪读舍人。沛王爷正请他回府议事。”
曹达打起官腔:“皇太子殿下的旨意,你敢违抗?”上前扶住王勃一个胳臂。
差官官腔更足:“没有沛王府殿下旨意,谁敢刁难王舍人?”也上前扶住王勃另一只手臂。
曹达笑着拖:“王公子,请!”
差官也笑着拉:“王舍人请!”
王勃巍然而立,纹丝不动。
“你放手!”差官拖着王勃冷面向曹达。
“你走开!”曹达拉着王勃恶脸对差官。
王勃眉毛一扬,蔑视一笑,轻轻挥臂就将曹达和差官甩得两边踉踉后退。他二人立即冲向对方,如斗鸡怒目相视。双方的随从也各为其主冲向前来,严阵以待。
憨儿勇敢上前护住了王勃。杜微关切地指曹达:“他是个阴死鬼,比蛇毒……。”
曹达一使眼色,他那一伙龙武军,拔出刀剑,逼住了赤手空拳的差官一伙。
曹达转向王勃强硬地:“请!”他见王勃冷冷微笑,傲立不动,又变脸变色奴颜卑下地乞求:“看在吴子璋大夫的面上,王公子你成全我这当奴才的吧!”
被刀剑逼住的差官喊叫:“王舍人,哪有这样挥刀舞剑召见客人的。你不能去冒险!”
曹达又软硬兼施:“公子若讲义气,就跟我走,否则……。”
“否则你要怎样?”王勃逼上前去双目圆瞪。
憨儿和杜微忙拦住王勃:“公子……”“贤弟……”
曹达又软了,拱拱手:“那……我只得请着不走,架着走了。”他向龙武军一挥手。
两个龙武军从身后胁下将王勃猛架起来,一个魁武的虎彪大汉,往他跨下一钻,王勃就骑坐在这高大汉子的肩上了。
王勃没有料到会有这一高招,被逗得笑了起来。
憨儿要追过去,被其他龙武军以刀剑逼住了。
王勃童心顿起笑道:“杜仁兄恕不远送。我要骑着马儿,闹儿戏去了!”
龙武军前护后拥拔腿奔跑。王勃猝然像个顽童骑人马,任他们连奔带跑,他竟大声喊叫:“冲啊,冲啊,得儿驾,驾……”
杜微、憨儿和杜微的行李挑夫,都被王勃的恶作剧闹得笑不是,责不是,忧不是,恼不是,难以表达各自的心情。”
王勃被架在人马上上了灞桥,差官等一伙高喊着:“你们不得无礼,把人放下……”紧追不舍到桥下。曹达指挥着龙武军以刀剑相逼在桥上。前一伙跑得快,后一伙追得急,就这样忽快忽慢,忽进忽站。王勃更是顽心玩皮大喊大叫,引得行人相随看热闹,一群孩子更玩笑起哄紧随不舍。
歌声起:哈哈哈,呵呵呵,
嘻嘻哈哈,哈哈呵。
人抬人高成奇货,
奇货可居要争夺。
争的争,夺的夺
机不可失夺王勃。
哈哈呵呵呵,王勃啊王勃,
哈呵哈哈呵,奇货啊奇货,
人才难得须囤积。
标上个“为国求贤”谁敢说。
哇哈哈,王勃啊王勃,
这样的礼贤下士谁见过?
哇哈哈,奇货啊奇货,
笑煞了不拘小节小王勃。
哇哈哈,哈哈呵,
哈呵哈呵哈哈呵,呵……
说书人:市场经济、奇货可居,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人抬人高也是古今一样,王勃啊王勃你算是什么奇货。他嘻嘻哈哈不知道,只有天知道,这是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