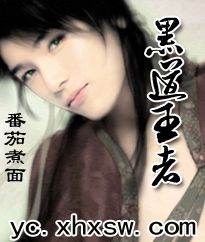第三卷 3 -- 第二章 剑圣之女
一日之后。
苦木集北向二百余里外。
这已在百合平原之外,山峦举目可见。
在一条于山梁上盘旋的山道上,有两人一前一后顺着山道向上攀登,一人身材伟岸,另一人则很是消瘦。
他们正是顾浪子、南许许二人。此时南许许已易容成另一副容貌,衣饰朴实,但收掇得干净利落,面目和善,乍一看极似一勤恳忠心的老家人,甚至连那张明显病态的脸容也被掩饰得了无痕迹。
他的肩上背负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手上还提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摆放着香烛、香纸以及一些果点,让人感到这像是一位老家人陪着主人去上坟祭奠亡灵。
南许许以为这是顾浪子为了尽可能不引人注意,才让他买了这些香烛、果点作掩饰。同时他觉得,这种方式也的确不错,至少常人决不会起疑。
但南许许却不知顾浪子为何要登上这道山梁,由山道的荒芜程度推测,这条山道显然不会通向另一个集镇、村落。南许许甚至怀疑这条山路恐怕至少有数月长时间不曾有人涉足了。
偏偏顾浪子说是要去见一个人。
由如此荒凉的山道攀上山梁,会见到什么人?南许许百思不得其解。
更何况,他们如今的处境十分不妙,如果在苦木集不是花犯有意暗示他们,恐怕他们早已逃不出四大圣地的追踪!顾浪子想见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可以让顾浪子不顾危险?
如今顾浪子的精力甚至还不如常人,所以两人的脚程并不快。南许许走在前面,用空着的手拨开乱草荆棘。
当山路绕过一块青灰色的巨岩后,开始变成不再陡峭,而是平缓地斜斜穿过一片枫树林。
当南许许穿过枫树林后,赫然发现前面出现了一片空阔之地,在空地的中央有一座坟丘,显得格外醒目。
南许许暗吃一惊,以至于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一直以为购置的香烛之类的物品只是为作掩饰之用,不曾料到在这儿真有一座坟墓。
“你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顾浪子忽然在南许许的身后问道。
南许许一怔,皱眉思忖了片刻,惑然道:“今日是九月二十四……但这似乎并非什么特殊时?”
“如今的九月二十四当然不是特殊的日子,但十九年前的九月二十四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顾浪子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在这样静谧的密林间,让人感到格外凝重。
“十九年前?”南许许若有所悟,他转过身来,望着顾浪子道,“十九年前,应是你我被不二法门追杀,朝不保夕的时候……”
顾浪子微微颔首,道:“正是。而十九年前的九月二十四,则是我被梅一笑梅大侠所‘杀’的日子!”
南许许先是一震,复而指着那座坟丘道:“莫非……那是你自己的坟墓?!”
“顾君满庭之墓。”
墓碑上刻下的字刚劲有力,深入石碑半寸,且无一处顿滞不畅,是出自梅一笑之手。
坟丘长满了青草,墓碑上也落满了尘埃枯叶,石碑底部有青苔的痕迹。虽然明知这墓其实是一副空墓,但这番情景,仍是让人感到不胜凄凉。
目睹这座别有一番来历的空墓,一幕幕往事浮上南许许、顾浪子的心头……
让南许许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在空墓前竟然依稀可见曾有人祭奠过的痕迹:半截已变得发白的未燃尽的香烛,插在墓碑前小竹筒中的香火……
难道在以往的日子里,顾浪子也会携香烛、烛香来祭奠自己?
若真如此,那此举真有些不可思议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顾浪子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人不会对他的死亡有所怀疑。但事实上以这种方式掩盖事实并无多少实际用途,因为一旦真的有人对顾浪子的死亡起疑的话,那么就不是半截香烛、几支香火能打消其疑心的了。
剩下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来此祭奠的人是顾浪子的亲人,因为除梅一笑、南许许及顾浪子本人之外,再无人知道真相——也许灵使是一个例外。
不过顾浪子是天阙山庄的传人,以天阙山庄当年的富豪,自然有专属天阙山庄的坟山,而顾浪子的坟墓却无法与其先祖修在一起,足见天阙山庄当年对这不肖之子的失望与不满,如此看来,来祭奠顾浪子的人是否是天阙山庄的人还值得怀疑。
当然,也许天阙山庄虽然大义灭亲,但对与顾浪子有血脉相连的亲人来说,这份亲情也是无法彻底割舍的,私下有人来此祭奠顾浪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南许许忍不住问道:“你以前也常来此地……为自己上一炷香?”
“每年我都会来此一次,但我从未为自己焚香祭奠。”顾浪子苦笑了一下,“毕竟我还活着。”
南许许道:“我可是第一次知道你还有‘满庭’此名,照理这名字应比‘浪子’这样的称谓文雅顺耳多了,但不知为何,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
“恐怕除了我的长辈之外,已没有几人知道我真的名字是顾满庭了。满庭……满庭……”顾浪子轻轻地重复着自己的名字,眼睛忽然湿润了,他缓缓地道,“我娘就是这么唤我的,最后一次听她唤我,已是二十多年前了。二十余年弹指而过,如今,她老人家恐怕已是白发斑斑了吧?而我除了让她老人家伤悲之外,竟不曾尽过一次孝心……”
他说不下去了,便转过话题道:“有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满庭’并非我从前的名字,而我一个兄弟、一个朋友的名字,他与我有一样的容貌、一样的出身,但他性情平和,并不执著于刀道。他老成持重,肩负着承延天阙山庄显赫家世的重任,并且做得极为称职出色……你明白我所说的话吗?”
南许许沉默了片刻,道:“你来此地想见的人是你的亲人?”
顾浪子道:“正是。”
南许许正色道:“你本不该如此!其实,顾满庭的确已死了,死于十九年前的九月二十四!活下来的不是顾满庭,而是顾浪子!十九年过去了,天阙山庄纵有伤悲,也会有所消淡了。若今日天阙山庄知悉你还活着,这消息一经传开,带给天阙山庄的恐怕不仅是惊喜,便会是一场灾难吧?”
顾浪子道:“你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我自有分寸。”
……
日已西斜。
坟丘周围的杂草已被南许许、顾浪子拔去,再无其他事可做时,两人便开始等待顾浪子想见的人出现。
眼见黄昏已至,四周归巢鸟儿的鸣叫开始渐渐增多,林中像是有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雾气在悄然弥漫开来,使人的视线慢慢变得模糊。
“也许你要等的人并非一定是在九月二十四来此地。”南许许也没有多少信心了。
“不,她一定会在九月二十四这一天来此的!”顾浪子很有把握地道。
南许许道:“但愿如此。”言罢,他将手伸入那只鼓鼓的包裹中,摸索了半天,似摸出了一点什么,紧握于手心,随后放入口中,咽了下去。他叹了一口气,道:“四大圣地定是受灵使唆使,才派出这么多年轻弟子寻找我们的下落。这些人虽然年轻,却也不可小觑!也不知他们怎会对你我起疑,若非花犯感念我救了他一命,恐怕那三个年轻人就够棘手的了。照此下去,我们恐怕又要长年疲于奔命,不得安宁了。如此一来,要找到可以压制我所中之毒的毒物也不易了。”他本是席地而坐的,说到这儿,他的身子向后一靠,倚靠于一棵树干上,闭目养神。方才他咽下的定是一至毒之物,此刻他要静心“消受”。
正当此时,却听顾浪子低声道:“果不出我所料,她果然来了。”
南许许依然闭着双眼,道:“虽然往日你的内力修为远在我之上,但如今却今非昔比了,怎可能我尚未察知你已先察觉?”
“你的说法不无道理,不过若我不是凭感觉,而是凭双眼,是否又另当别论?”顾浪子道。
南许许一下子睁开双目,坐直身子,立时看到正有一女子穿过枫树林向这边而来。因为天色渐暗,相隔有些距离,暂不能将其看清楚。
南许许心道:“此人与我已颇为接近,我却丝毫未察觉,看来她的修为不弱,不愧是天阙山庄的人。”
恐怕那女子不会料到在这样的黄昏时分,会有人守候于荒坟前。南许许想到这一点,担心那女子受到惊吓,于是先干咳一声,以作提醒。
那女子的脚步倏止,目光迅速扫向他们这边。
但很快她便恢复了常态,继续向这边靠近。
南许许忽然发现顾浪子的脸上隐有惊愕与意外之色。
是什么事让顾浪子感到意外?难道前来的女子并非顾浪子预料中的那女子?
但此刻南许许已不能开口询问,因为来者与他们越来越近了。
这时,南许许已看清来者是一位年约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容貌清丽脱俗,身材修长曼妙。如此佳丽,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出现,多少有些不协调,但见她一袭素白衣裳,且未着脂粉,手中拿有香烛、香火,又显然应该是来顾浪子坟前祭奠的。
南许许心中飞速转念,揣度着这美丽少女的来历。按理既然此人是顾浪子的亲人,那么她与顾浪子的五官容貌应有相似之处,但顾浪子这些年来受尽磨难,其容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脸上皱纹纵横,这与此少女的水肌雪肤委实难以联系在一起。不过,从身形来看,此少女的挺拔高挑与顾浪子的岸伟倒有些相似之处。
奇怪的是那少女看顾浪子时的眼神与看南许许时的眼神没有什么不同,而当少女靠近时,顾浪子既未开口,也未有其他任何表示,让人感到他与这少女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倒是那少女先开了口,她看了看坟丘那边,大概是留意到坟丘四周的杂草已被拔去,道:“二位爷爷也是来拜祭此亡灵的?”
南许许被少女称做“爷爷”倒在情理之中,而顾浪子其实不过四旬,只是因为二十年的逃亡生涯使他格外显得苍老之故,才让少女有了错觉。
顾浪子当然不会在乎这样的小事,他十分友善地点了点头,道:“姑娘也常来吗?”
那年轻女子摇了摇头,略略犹豫了一下,却还是道:“以前是我娘来的。她每年都会来一次。”
南许许恍然大悟!心道:“原来顾兄弟要等的人不是这位小姑娘,而是她的母亲!难怪他们两人似乎都互不相识,十九年前,恐怕这小姑娘还没有出世呢。”
顾浪子叹了一口气,道:“这样的荒山野岭,也真难为你娘了……为何这一次她没能来?”
顾浪子后面的话像是随口所问,但对顾浪子十分了解的南许许来说,却已听出顾浪子问到此事时颇有些紧张不安。
那少女双目一红,幽幽地道:“我娘她……病了,不能前来,所以吩咐我代她前来。”
“她……病了?”顾浪子身子微微一震。
由少女忧蹙的神情,谁都可以看出她母亲的病绝对不轻。
南许许见顾浪子对少女的母亲十分关切,暗自忖道:“顾兄弟‘浪子’之名是名副其实,他年轻时恐怕不知有多少红粉知己,这少女之母会不会也是其中之一?”
想到这儿,南许许开口道:“姑娘,不知这墓中之人是你什么亲人?”
那少女迟疑了一下,言辞闪烁地道:“墓中人生前是……是我娘的故友。她实在不是一个善于说谎的女孩,说完这些,竟连目光也不敢与顾浪子、南许许正视了。
南许许暗叹一声,心道:“这小姑娘似乎阅历甚浅。顾兄弟的身份独特,与他有关联的亲友面对陌生人显示有所隐瞒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她却很是不安。幸好这次她遇见的是我与顾兄弟,若是遇见不二法门的人或是顾兄弟的其他仇家,她恐怕要吃大亏了。而灵使已知顾兄弟还活着,那么他要设法由这空墓查找线索也并非不可能……”
想到这些,南许许眉头微微皱起。
那少女默默地取出带来的香烛、香火,将香烛点起,摆好果点祭品,焚香跪叩。
顾浪子神情忧虑,默默地望着那少女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而南许许也同样沉默着。
等所有的香纸焚尽时,天色也已完全黑了下来。
眼见那少女已拜察完毕,南许许上前帮她一道收拾了祭品,随后问道:“姑娘,天已黑了,你还要独自一人赶回家吗?”
那少女道:“正是。”
“那你一路上要多加小心。”顾浪子关切地道。
那少女道:“谢谢爷爷。”施礼后,循着来时的路向山下走去。
“这孩子,竟不知盘问我们的来历。”当那少女远去之后,顾浪子既感叹又怜惜地道。
“若你我真是居心叵测之人,她盘问了又有何用?难道我们会如实相告吗?”南许许道。
顾浪子赞同地点了点头,随后道:“你在帮她收拾祭品时,应该已做了手脚了吧?”
南许许叹了一口气,道:“我就知道你会有追踪她的打算——你是否想到此举有可能给她们母女二人带来危险?”
顾浪子也叹了一口气,道:“她母亲如果不是病得很重,一定会来的……”
“你是想让我救她?”南许许道。
顾浪子点了点头。
南许许轻轻地笑了一声,道:“其实即使她没有重病,你也很可能会打算去见她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择在今日来这空墓前了。”
顾浪子未说什么,等于默认了。
南许许叹道:“我猜到你的想法,虽然我不赞同你的决定,但我的确在帮她收拾祭品时做了手脚,如果你执意要去见她,那么她永远无法逃过我们的追踪,除非她已将带来的东西全扔了,并且在扔之前从未接触它,但这已是不可能了。”
“我的确不能不去见她,她是我唯一的姐姐,梅一笑梅大侠已去世,留下她们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我怎能在她重病之时仍不闻不问?”顾浪子道。
“姐姐?!”南许许一怔。
随即他自嘲地笑了笑,无声地笑。
夜色中,顾浪子的声音道:“那小女孩叫梅木,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她,但我曾在四年前见过刑破,刑破追随梅一笑梅大侠之后,就再也没有背离他们一家人,我对刑破不必隐瞒什么,也是刑破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梅一笑梅大侠和我姐姐的一些情况。”
“四年前?”南许许讶然道。
“也就是我暗中随战传说、不二法门的黑衣骑士进入西部荒漠中的那一次。”顾浪子解释道。
“刑破……梅木……”南许许在心中默默地把这两个名字念了一遍,心中微有悸动,似乎想到了什么,但那种念头却是极为短暂缥缈,无法真正地捕捉。
心念一闪即逝,南许许想要细辨,却已不可能。
正如南许许所言,他们能够准确地追踪梅木。先前正是凭借相似的方式,南许许追踪晏聪,并且找到了顾浪子。
梅木下山后一路北行。
南许许与顾浪子追随梅木的行踪已有半个多时辰了。
南许许低声道:“梅一笑隐居之地离这儿究竟有多远?”
“我也不知。”顾浪子道。
南许许有些意外地道:“你不是说刑破曾告诉你不少事情吗?”
“但我唯独没有问梅大侠的隐居之地,因为对于一个淡出武界的人来说,也许许多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最在意的反倒是那份真正的与世无争的淡泊、清静。”顿了顿,顾浪子又补充道,“也许,我之所以不问梅一笑的隐居之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担心有一天我会忍不住去见我姐姐,从而为他们带来危险——但今天我仍是违背了我的初衷。”
梅一笑是顾浪子的姐夫,但顾浪子却更愿意称梅一笑为“梅大侠”,而非姐夫。
南许许道:“小姑娘独自一人来坟地,那么她们所居住的地方与坟地应该不会相去太远。”
……
月上树梢,秋夜凉意沁心。
一路追随梅木的顾浪子、南许许行至一条宽约五六丈的河前,河的对岸有木屋背倚绝崖构建,河面上有一座简易的浮桥连系河两岸。
由地势、地形推测,过了桥到达木屋之后,将再无其他途经向前延伸了。木屋有柔和的灯光透出,灯光更衬得木屋后的危崖狰狞高峻。
顾浪子、南许许站在河的这一边,望着河对岸的木屋。
南许许很有把握地道:“那间木屋,应该就是小姑娘最终的目的地——或者说就是梅一笑的隐居之地了。这里依山傍水,实是一清静之地。”
说到这儿,他看了顾浪子一眼,道:“是否心意已定?现在改变主意还为时未晚。”
顾浪子摇了摇头,道:“如果说先前我还多少有些犹豫的话,那么此时我则是决不会改变主意了,至亲之人近在咫尺,又在重病中,我岂能置若罔闻?”
南许许道:“我料定你必会如此。”
木屋四周收拾得干净整洁,屋内透出的灯光映照着屋外小院中的花花草草,其情形颇有农家庭院的宁静安详。
南许许、顾浪子一前一后穿过小院,刚走近小屋,便听“吱呀”一声,木屋的木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高挑窈窕,正是梅木。
三人打了一个照面。
梅木吃惊非小!以至于过了少顷她才愕然道:“你们……怎会来此?!”
顾浪子自忖自己与南许许突然在此出现的确出人意料,他担心会引起对方更多的误会,故决定及时说明真相。
于是,顾浪子直言道:“梅木,你放心,我们对你绝无恶意……”
“你……怎知我的名字?”未等顾浪子说完,梅木已失声惊问。
“因为……我是你娘的远亲。”顾浪子道,“听你说你娘病了,恰好我的这位朋友精于医道,故特意前来。”
他终是担心若说自己就是本应已死去十九年的顾浪子,会让梅木受惊。
梅木脸上闪过狐疑之色,她语气有些淡然地道:“自我出生之后,我娘就未与亲友有任何来往,所以即使是我的至亲,除我父母之外,也不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的!”
警惕之心,溢于言表。
顾浪子反而有些欣慰,心道:“先前感到她似乎阅历甚浅,这一次倒颇富心机。”
口中道:“个中详情,非一言能尽。不过,我带来一物,只要你将它交给你娘,你娘就自然知道我是什么人。”
说着,他取出一只以青铜打制而成的雀状物,其形扁平,轮廓简朴却唯妙唯肖。
梅木犹豫了一下,默默接过铜雀,轻声道:“两位爷爷先进屋中小坐,待我去问问我娘,只是我娘病得很重,不知她能否清醒识出这铜雀。”
说着,她侧身将顾浪子、南许许让入了木屋,并招呼他们在前堂坐下,敬上茶水后,这才到后室去见她母亲。
前堂转眼间就只剩顾浪子、南许许两人了,四下打量,只见前堂布置得很简单洁净,与小院中的情景大致相仿。
等了一阵子,却久久不见梅木出来,两人都有些不耐了,南许许尤是如此。他忍不住站起身来,在前堂来回踱步。
“会不会是我姐姐她碰巧此时病情加重,梅木一时抽开不身?”顾浪子不安地道。
南许许听顾浪子这么说,便停下了脚步,像是想起了什么,皱了皱眉,用力地吸了吸鼻子,又沉吟了片刻,喃喃道:“奇怪……”
顾浪子忙道:“有何奇怪之处?”
“既然你姐姐身染重疾,为何我却未闻到在这木屋中有任何药味?难道她从未服过药?”
这种可能性极小!
而南许许的医道修为已臻出神入化之境,对药性、药味、药的气息、功效无不是洞悉入微,他既然断言在这木屋中没有闻到药味,就决不会有错。
顾浪子既惊且惑:“难道,是梅木未说实话?但她又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南许许眉头越皱越紧,倏地,他失声惊呼:“我们上当了!”
顾浪子霍然起身,惊道:“此话怎讲?”
南许许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我所见到的年轻女子,根本不是你姐姐的女儿梅木!”
“为什么?”顾浪子大吃一惊。
“因为刑破!”南许许飞快地道,“按理,刑破早该出现了,在梅木前去空墓拜祭时就该出现了,刑破不可能放心让梅木一人独自前去空墓!”
事实上,尚在空墓前时,南许许就已隐约有所警兆,但最终却只是一闪而过。
顾浪子还待再说什么,南许许已一把拉住他,急切地低声道:“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此屋……”
“就算梅木未说真话,也未必就说明她不是真正的梅木……”顾浪子已有些语无伦次了,从感情上说,他宁可南许许的推测是错误的。
倏地,木屋四周几扇窗子同时爆响,窗棂四碎,碎片横飞。
人影闪动!
“嗖嗖嗖……”箭矢由几个方向同时向南许许、顾浪子立足之处射至,来势甚疾。
南许许一把抓起身边的木桌,顺势一抡,“笃笃笃……”连串撞击声惊心动魄,箭矢来势奇猛,木桌虽然抡转如飞,对射于其上的箭矢产生了极大的横向撞击力,但绝大部分的利箭竟都射穿了木桌,随后向各个方向跌落。
顾浪子虽曾纵横刀道,但此时却几近丝毫不谙武学的人,面对来势凌厉的飞箭,他只能徒呼奈何。若非有南许许相助,第一轮箭矢的攻击就足以置顾浪子于死地。
事发突然,顾浪子又毫无战斗力,而对手又在屋外暗处,南许许空有一身杀人于无形的毒功,也难以发挥作用,明智之举显然是尽早从这种被动不利的局面中抽身退走。
便要想全身而退又谈何容易?南许许心知今夜只能是全力一搏,能否逃离险境,就看造化如何了。
险险避开第一轮箭矢,南许许一把挽住顾浪子,向一侧贴地滚去。
他所取的方向,是他依据箭矢的来向判断出的唯一有可能没有隐伏对手的方位。
“剁剁剁……”劲箭在南许许、顾浪子贴地滚过的地方迅速排列成一条线,并循着南许许、顾浪子所取的方向飞速延伸,只要南许许的速度略有滞缓,就必会立即被乱箭钉死于以木板铺就的地面上。
转瞬间,南许许挽着顾浪子已滚至前堂的一侧边缘,木壁矗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南许许毫不犹豫地弓腰耸肩,借身躯一曲一弹之力奋力跃起,背向木壁,全力撞去。
“哎哟……”“砰……”顾浪子的痛呼声与木壁被撞得洞开的声音同时响起,看样子顾浪子已被箭射中了,但由他的痛呼声听来,应该不是致命伤。
南许许自忖撞开木壁进入内室后,因为空间的变化,伏击者形成的包围圈也许会出现空当,加上内室空间狭小,有利于他利用毒物发动突袭,也许能赢得脱身之机。
这少许的欣慰才刚刚浮上他的心头,蓦闻顾浪子惊呼一声:“不好!”
南许许一震之余,立即明白顾浪子何以如此惊呼。
因为他们撞开木壁之后,本应在极短的瞬间便要跌落地上的身躯,竟仍在一个劲地下坠!
木壁之后,根本不是内室,反而更像是无底的深渊!
南许许忽然一下子明白过来,方才他所推察出的伏击者唯一的空当,其实根本不是可以借其脱身的空当,而是一个陷阱!对方是有意将他们引至这个方向。
下坠的速度迅速加快,耳边风声呼呼。
即使只有一人,以南许许的修为,也未必能够缓止下坠的速度,更何况他还身负顾浪子的重量,而且又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坠落的,重心已完全失去。
南许许颇有万念俱灰之感。
对方既然设下了这一陷阱,那么就完全可能在下方设上尖刀等致命之物,偏偏此时南许许、顾浪子只感到四周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任何物什,只能由呼呼的风声来感觉自己的飞速下坠。
两人心头同时升起几乎相同的念头:“没想到亡命天涯这么多年,竟在今日以这种方式结束性命!”
就在两人都已绝望之时,他们身躯下坠的过程终于终止!
却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在坚石上撞个粉身碎骨,也没有被利刃贯体,而是重重地撞在一张冰凉、坚韧而有弹性的网上。
两人的身躯撞在网上,立时再度弹起。
但就在他们的身子撞在网上的同时,上方响起了铁物轧轧之声。两人的身子刚刚弹起,立即又撞在了粗大的铁栅上,再度落下。
最初下坠时毫无遮拦,而弹起时却撞上了铁栅,可见是在他们的身子刚撞上那张不知以何物制成的网时,启动了机括,上方的铁栅及时弹出,正好挡住了顾浪子、南许许二人。
这一次下落撞在网上时,南许许立即及时用手扣住网眼,稳住身形,以免再一次弹起——当然,他也知道这一举止丝毫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已落入圈套,并被困于此!
等两人的身形完全稳下来之后,南许许赶紧问道:“顾兄弟,你伤在什么地方?”
“右臂……无妨。”顾浪子道。
南许许知道顾浪子本不是伤在要害处,但他担心在方才的跌撞中,那支箭又会对顾浪子造成新的伤痕。
随即顾浪子又道:“看样子,伏击我们的人其实并不想立即取我们性命,否则,‘迎接’我们的就不是这张网了。”
两人说话时,声音在“嗡嗡”回响不绝,就像是在井中说话。
“也不知他们看中的是我这把老骨头,还是你这个酒鬼。”南许许道。
顾浪子所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压低了声音道:“既然这个梅木是假的,那岂非……”后面的话,他未说出口,但意思却十分明了。
未等南许许开口,黑暗中已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真正的梅木姑娘当然已被老夫所控制。”
声音就在顾浪子、南许许两人的正上方!
赫然是灵使的声音!
忽然有火光亮起,黑暗退去了。南许许、顾浪子终于可以看清自己的处境。
此时他们正躺坐在一张泛着乌光的网上,此网不知以何物织成,网线如麦秆粗细,网的四周嵌入石壁中,下方凌空,透过网眼向下望,隐隐可见波光粼粼,不难推断,这下方的水与南许许、顾浪子进入木屋前曾经过的小河十有八九是相连的。
四周是平整的石壁,再往上看,灵使正站在横封于两人顶上两丈多高的铁栅上,居高临下地望着他们,在灵使的身旁,有数人手持火把站着。
无疑,这是一个构造紧密的地下囚室!而这样的囚室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筑成,它应当已存在了颇长的时间。
在这种情形下,被对方以居高临下的目光相望,南许许、顾浪子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灵使像是有意要彻底摧垮他们的尊严与自信,他道:“论武道修为,你们已败在本使手下;论智谋,你们同样是无法逃脱本使的运筹之中!本使只是暗使小计,就足以让你们自投罗网!”
顿了一顿,灵使继续道:“事实上早在本使推测顾浪子还活着的时候起,本使就已开始留意那座空墓,从而也借空墓为线索,找到了梅一笑的隐居地。梅一笑之妻,亦即顾浪子的胞姐母女二人的行踪早已在本使的掌握之中,但本使一直未惊动她们,一则因为梅一笑乃世所公认的侠者,不二法门没有必要惊扰他一家人;二来本使也担心打草惊蛇,让顾浪子你有所警觉。直到前些日子真正地确知你还活着,而与你一战又让你侥幸逃脱,本使才想到利用顾影母女诱擒你们,果然一举而成。
“顾浪子,本使宽宏大度,可以告诉你顾影并没有身患重疾,她们母女二人是在前去拜祭空墓的途中被本使将她们请去另一地方,你放心,本使不会为难她们。梅一笑曾救过你一命,你对梅一笑十分敬重,而且你与唯一的姐姐顾影自幼便十分融洽,所以当你听说她身患重疾时,你不可能置之不理——剩下的事,其过程不需多说,你们也应想象得到吧?”
顾浪子沉默了良久,方缓声道:“看来,你对顾某的性情倒了解不少。”
灵使淡淡一笑,道:“你莫忘了,我乃不二法门四使之中的灵使。察人心灵,有如洞烛,这对本使而言,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顾浪子道:“是吗?相信你之所以没有立即将我们除去,以绝你心头之患,定是你还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不过,你自诩能察人心灵,有如洞烛,不知可曾洞悉我们宁愿赌上两条性命,也不会让你如愿以偿?”
灵使正色道:“若连这一点都不能看透,本使岂非枉称一个‘灵’字?本使相信你们可以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但同时本使却也相信有些人的性命,你们却不能不顾!”
顾浪子神色倏变!
他嘶声道:“你是说梅木母女?!哼,片刻前,你还声称决不会为难她们,此刻却已食言!枉你好歹也是有脸有面的人!”
顾浪子只恐灵使对顾影、梅木母女二人有所不利,故有意让灵使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便过于反复无常。
灵使哈哈一笑,道:“顾浪子,你不必再自作聪明,没有顾影母女二人,本使同样可以让你就范!”
说到这儿,他再也不多看顾浪子、南许许二人一眼,转身离去。
如果说顾浪子二人被困处所有如一口深井的话,那么方才灵使所立的地方就是深井的中部,而灵使离去的横向通道,显然可以通达地面。
谁会料到一间木屋下面,竟有这一番天地?
南许许、顾浪子甚至相信他们所见到的、发现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木屋的下面,定还有更为错综复杂的结构。
灵使离去之后,他身边的几个人也随之离去了,一切又重新陷于黑暗之中。
方才有火光时,南许许已看到了顾浪子的箭伤所在的具体部位,这时他对顾浪子道:“让我先将你所中的箭拔出吧。”
很快,他就摸到了射入顾浪子右臂的利箭。南许许在黑暗中解开一直随身携带的包裹,包裹中有他视如性命的奇药、奇毒,黑暗丝毫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因为他对这些药的熟悉程度,决不亚于对自己十指的熟悉,很快南许许便找到了他所要的药。
随后,他的右手五指在顾浪子箭伤伤口部位的四周以快不可言的速度飞快游走,似乎在寻找什么,又像在酝酿什么,冷不丁地,南许许右手食指、中指一曲一扬,一挟一带,箭已被拔起!
而顾浪子几乎没有感到有任何痛感。
早已准备好的药洒落在了伤口处。
顾浪子知道不出几日,他的右臂必会恢复得比原先还完好。
他这才道:“老兄弟,灵使既然否认了会利用梅木母女要挟我,那么他还可以凭借什么予我们以压力?”
南许许笑了笑,道:“看来,灵使说他能察人心灵有如洞烛,也并非完全是夸大其词,至少他知道如何才能让你心存顾忌,从而他便可在心理上占据主动。如今哪怕其实根本没有他人落在灵使手中,你也顾虑重重了。”
顾浪子恍然道:“言之有理!”顿了顿,转而道,“此处如此清静,且也不必再担心被人察觉行踪——美中不足的就是少了一壶美酒。”
戏言之中,充满了自嘲与沧桑感。
南许许拊掌大笑,笑声一样的怆然。
待他笑毕,顾浪子方道:“你说你我能暂且活下来的原因何在?”
南许许沉吟了片刻,道:“莫非,是因为灵使想查出‘他’的下落?”
南许许隐晦地以“他”指借了某一个人,但顾浪子却是对南许许所指的人物心知肚明,他道:“十有八九就是因为这一原因。”
井状的地下囚室一下子静了下来。
竟能听到下方“淙淙”的流水声——看来下方的水果然与那条小河相连。
“他”,究竟所指何人?
坐忘城。
经历了一次浩劫后的坐忘城,经过了一些日子后,总算恢复了平静——至少,表面上是平静了。
被毁坏的城墙、城门已修复,被焚烧过的乘风宫也开始逐步修葺。
只是,西城山腰上多出的坟墓,却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坐忘城万民:曾有一场劫难降临于坐忘城。
除此之外,还有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在坐忘城城东门外竟修建起一间茶寮,茶寮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沏的茶也一律是新茶,茶寮的主人是一个剑帛人,与所有的剑帛人一样:白净、和气、精明。
奇怪的是这间茶寮竟不是搭建在路边,而是搭建在与道路有些距离的土岗上。
初时茶寮的出现让坐忘城中人感到十分意外,并多少心存顾忌,于是先后有人前去茶寮明察暗访,结果是并未发现此茶寮有何不妥,反而无意中成全了茶寮的生意。茶寮所沏的茶无论火候、工艺皆是不凡,以至于有半数的人成了回头客。
随后,茶寮前树起了一块大招牌,上书斗大的“双城之语”四个大字,即使站在一里之外也能将招牌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
乍一看,“双城之语”四字与茶寮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干,反倒是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前不久的卜城、坐忘城之战。卜城、坐忘城双城之战曾震撼乐土,当然能吸引人注意,但那毕竟是一场血淋淋的残酷争战,若是直接将之与茶寮联系在一起,只怕会让人反感。
而一个“语”字却不见丝毫兵刃血腥气息,偏偏又能巧妙借用双城之战来引起人的好奇之心,以至于树起“双城之语”这一招牌后,路经此地的人几乎一无遗漏地会爬上土岗,进入茶寮。
而茶寮的主人也并非仅以四字招牌做噱头,在茶寮中还可以见到卜城的战甲、兵器,喝上卜城独有的奶酒,触摸名满乐土的卜城特产龟甲雕。当然,这儿亦有富有坐忘城特征之物,尤为醒目的是一只风干制成的灰鹰,被固定在一木柱上,栩栩如生,让人一下子想到了与坐忘城有关的传说。
面对众茶寮几乎一无例外地会问到何以称“双城之语”,茶寮的主人总是很自谦地声称:“鄙人姓物名语,来往的客人多是双城的朋友,茶寮的生计,就是依仗双城,双城即是鄙人的衣食父母,鄙人物语自是属于双城之‘语’!”
似乎不无道理。
但显然这招牌有似是而非、出奇制胜的巧妙。
本应生意清淡的茶寮竟甚是红火。
与“双城之语”茶寮的红火相反,坐忘城内却透出了往日所少见的冷清。
重山河战亡,城主殒惊天前往禅都,凶吉未卜,昆吾为救护城主殒惊天,也已远赴禅都,坐忘城重要头领有近半不在城中,冷清是在所难免的事。
南尉将伯颂对坐忘城实力空虚的局面多少有些担忧,唯一能让他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殒惊天已在前去禅都的途中,冥皇再难找到借口发动其他势力围攻坐忘城。
除了担忧坐忘城的局势、殒惊天禅都之行的安危外,伯颂还牵挂着老友石敢当。石敢当已前往天机峰,虽然石敢当本是天机峰道宗宗主,但在伯颂看来这并不能保证石敢当此行定能安然无恙,白中贻的事就已是预兆。石敢当离开坐忘城前往天机峰时,伯颂等一干人为其送行,察觉到石敢当的神情有些异样,作为与石敢当相交数十年的老友,伯颂推知石敢当必有心事。
虽有所担忧,但在伯颂看来,毕竟石敢当是道宗昔日宗主,此次天机峰之行就算有所波折,也决不会有性命之忧。而远涉禅都的殒惊天才是真正处于生死存亡之境!
只是伯颂不会知道,他的预料并不正确……
天机峰。
天机峰乃映月山脉的最高峰。非但如此,天机峰同时也是映月山脉群峰山势最复杂多变的山峰之一,忽而峭壁陡立,忽而洞穴幽深。
清晏坛是道宗重地,修建于天机峰峰巅,是道宗宗主的清修之地,也是收藏道宗宝珍之地。比如新近为道宗得到的“九戒戟”就是藏于清晏坛。
清晏坛的安危本是由道宗三旗主轮流负责,可自蓝倾城成为道宗宗主之后,修改旧律,改由蓝倾城两大嫡传弟子伏降、韦惊及其统领的三十六坛士守护。蓝倾城修改旧律的理由是担心三大旗主既然是轮流守护,恐怕就有可能出现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蓝倾城这一说法不无道理,故未遭到什么质疑。
清晏坛的一间密室。
油灯如豆,一室昏黄,外面的绚丽阳光根本无法照进这间密室。
一枯瘦老者被特制的锁具牢牢地困锁住了,手足虽可活动,却无法挣脱,因为一旦运起内家真力,其双手脉门立时被扣紧,真力再难为续。
昏黄油灯隐约可以照出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他,赫然就是石敢当!
密室以坚石砌成,连唯一的一扇门也是石门。
这时,密室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少顷过后,石门忽然缓缓地滑开了,只有极为轻微的声音,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扇石门!
一容貌威仪、相貌堂堂的男子出现在石门外。此人五官衣饰都予人以精心修饰过的感觉,乍一看,颇为年轻,但再细看时,却又像应在五旬左右年纪,很难作出准确判断。
在他的身侧,是一个三旬左右的男子,身形矮壮,比前者足足矮了一个头。此人目光如炬,显得精力旺盛,让人不敢小觑。
矮壮男子是负责守护清晏坛的伏降,而与他一同出现的人则是其师蓝倾城。由于蓝倾城保养得很好,从外表上看,很难看出他们是师徒关系。
石敢当本是微合着双目,为声音所惊动,缓缓地睁开眼来。
蓝倾城缓缓步入密室内,居高临下地望着石敢当,笑了笑道:“老宗主,你受委屈了。”
石敢当神色平静,没有出声。
蓝倾城也不尴尬,自顾接着往下说:“蓝某之所以如此对待老宗主,实在有情非得已之处。”
石敢当本是平和的目光倏然暴现精光!刹那间,本是枯瘦苍老,又被困缚的石敢当竟有凌然之势,一直做胸有成竹状的蓝倾城忽然感到莫名的心虚与惊悸,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随即他便意识到石敢当已被牢牢控制,根本无法对他形成威胁时,方暗自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些恼羞成怒。
石敢当缓声道:“蓝倾城,你心虚了。”
蓝倾城哈哈大笑,笑得很是张狂!笑毕,他不屑地道:“蓝某在宴席上出手擒你,至今道宗内无一人就此事说一个‘不’字,无一人为你求情,足见本宗主早已成为道宗人心所向!虽然你昔日曾是宗主,但二十年过去了,你已是孤家寡人,若以为在道宗你还能呼风唤雨,就未免太天真了!”
伏降在一旁道:“石敢当,当年你弃道宗大业于不顾,私自离开天机峰,一去二十年不回,早已让道宗上下怨声载道。二十年后你走投无路,返回天机峰,若安分守己,宗主念你年岁已高,自会让你在天机峰颐养天年,聊度残生,可恨你竟不自量力,宗主好心设宴为你接风,你却不识抬举,冲撞诽谤宗主,实是自取其辱!”
石敢当连正眼都不看他,沉声道:“黄书山、白中贻是为何而死?你们应该心知肚明!设宴是假,毒害我是真,否则何以在宴席上只见你的亲信,而不见昔日为我所倚重之人?蓝倾城,我早已料到一旦我回天机峰,你一定会急欲除去我而后快!只是没想到你会那么明目张胆。如此看来,今日道宗,的确已面目全非了。”
蓝倾城略显诡秘地一笑,道:“恐怕出乎意料的不仅仅是这些吧?”
石敢当默然无言。
蓝倾城背负双手,在密室中缓缓踱步,边走边道:“二十年前,你的‘星移七神诀’修为已臻惊人境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本宗主自忖以自身的修为,毫无胜过你的把握,但事实上你我在宴席上交手,你却完全处于下风,其中原因,恐怕只有你我二人知晓吧?”
石敢当眼中流露出极为复杂的神色。
蓝倾城对自己言语的效果很满意,他终于说出了最为关键的一番话:“在你修炼‘星移七神诀’时,因为某种原因,你的体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缺陷,或者说是种下了可怕的祸根,每当酉、戍之交的时候,你的内力便会突然消减过半。这对于一个武道中人来说,显然是致命的缺陷,因为一旦这一点被仇敌所利用,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你全心全意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以免日后为自己带来祸患,包括如黄书山这样的心腹,你也未向他们透露半句。”
说到这儿,他有意停顿了片刻,予石敢当一个揣测的空间:他当然从未曾是石敢当的心腹亲信,又如何能知道这一点?
石敢当虽然依旧沉默,但他心头的震动其实极大!
正如蓝倾城所言,他的内力修为的确是存在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致命缺陷。这个秘密,他只告诉过两个人,而这两个人是绝对不应会出卖他的——至少石敢当深信这一点。
但事实却显然出乎了石敢当的意料,蓝倾城知悉这一点,就证明这两个知情者当中,至少有一人将他的秘密传开了。
石敢当心头之震撼可想而知!回到天机峰的当天夜里,蓝倾城便设下宴席为他接风,石敢当对蓝倾城的所作所为早已愤慨不已,但他自持身份,当然不能立即鲁莽至甫一见面即出手,既然蓝倾城设下宴席,石敢当正好要借这机会将蓝倾城的真面目揭穿。
蓝倾城设下宴席,决不会是真的出于对老宗主的尊重。对于这一点,石敢当心中清楚至极,宴无好宴。但石敢当暗忖蓝倾城一定对他的武道修为有所忌惮,只要自己在其他方面多加小心,蓝倾城就无能为力。
而石敢当之所以作如此信心十足的设想,是基于坚信蓝倾城不会知道他的秘密,故他的“星移七神诀”能对蓝倾城形成足够威慑的前提下的。
没想到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宴席之中,石敢当当众指摘蓝倾城在道宗所犯下的种种罪责,蓝倾城竟毫不示弱,其亲信弟子亦借石敢当二十年前私自离开天机峰大做文章,群起发难,席间共有一百余人,竟无一人为石敢当说话!这已让石敢当大感意外,而更意外的是蓝倾城最后竟然主动出手,似乎根本无惧于石敢当名动天下的“星移七神诀”!
其时正是酉、戍之交,石敢当的内力修为仅及平时一半,以致在蓝倾城的攻击下受挫被擒。
石敢当一直以为这只是巧合,蓝倾城骤然发难时正好凑巧是酉、戍之交。
但蓝倾城方才所说的这一番话却彻底否定了石敢当的猜测!蓝倾城在酉、戍之交时发难并非巧合,而是有意而为之!
“蓝倾城何以知道我的秘密?”石敢当大惑不解。
而最让石敢当在意的并不是蓝倾城知悉这一秘密,而是他本坚信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决不会将此事向外人透露,因为那两人是他此生最信任的两个人。
蓝倾城站定了,以很是恳切的语气道:“老宗主,你一定在想如此机密的事我蓝倾城何以知道吧?不错,这一秘密本应是你最信任的人才有可能知道的,可是你忘了,这世间只有绝对的利益,没有绝对的亲友!唯一可以永远信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自己!”
石敢当忽然失声笑了,不无讥讽地道:“蓝倾城,你费尽心思将老夫擒住囚押于此,却既未取老夫性命,也无其他举措,难道将老夫一连囚押数日的目的,就是要让老夫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蓝倾城倒很沉得住气,他依旧不疾不徐地道:“蓝某从未要取老宗主性命的意思,只是因为老宗主对蓝某有些误会,为了道宗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安定大局,蓝某只好出此下策。如今,蓝某只想向你打听一个人的下落,老宗主若愿意说出,那么从此在天机峰老宗主是去是留都悉听尊便。”
石敢当轻叹了一口气,道:“你们将我囚禁在此这么久,就是为了向老夫打听一个人的下落?如此看来,此人必定十分重要了。”
蓝倾城见石敢当口气并不强硬,似乎有商量的余地,心中暗自欢喜,道:“其实也并不如何重要,甚至此人如今在乐土武道藉藉无名。”
石敢当扫了他一眼,道:“话已至此,何必再拐弯抹角?”
他心中道:“蓝倾城必然是一直欲除我而后快,那样他才会感到在宗主这一位置上能坐得安心。能让他暂时放弃取我性命的机会的事,必是非比寻常。我倒应借这个机会,从他口中套出真相。”
但蓝倾城比他想象中更沉不住气——或者也许是因为蓝倾城认为既已完全控制了石敢当,故他不必再有任何顾忌。
蓝倾城道:“蓝某要找的人,就是一直在玄流三宗内暗中传说的‘天残’!”
“天残?!”石敢当心头微微一震,似有所悟。
“当年,玄流先祖天玄老人神功盖世,但天玄老人一生却从未亲传弟子,其中原因,在之后的玄流三宗的历代弟子心目中,一直是一个不解的谜。与此同时,在三宗内,私下里还有一种说法,那便是天玄老人并非没有亲传弟子,只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是一个永远无法拥有内力修为的人,传说此人之名即为‘天残’。之所以有此名,是因为他自出生之日起,便天生残缺,注定他一辈子也无法修炼内力修为。
“对于这传说,玄流三宗所属有的深信不疑,有的却与之相反。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所谓的天玄老人的唯一亲传弟子从未真的出现过,一切都只是始于口头相传,止于口头相传。老宗主,你在二十年前就已是三宗宗主之一,对于这种说法,当然是早已有所闻,蓝某也不必赘言,而蓝某所要告诉老宗主的是,蓝某已确知‘天残’是确实存在的!”
说到此处,他的话头倏然而止,只是目不瞬转地望着石敢当,似乎是要从石敢当的神情变化中窥出什么。
石敢当脸上古波不兴,蓝倾城暗暗失望,但话已至此,他只能接着往下说:“蓝某已确知,老宗主你必然知道天残身在何处。论辈分,天残是蓝某的师叔,将他老人家请至道宗,是做晚辈的应尽的孝心。再则,如今三宗对峙,若能得到天玄老人唯一亲传弟子的支持,那么在道义上,道宗就将稳稳地占据优势。”
石敢当缓声道:“如此说来,你是处处为道宗着想了?”
“蓝某乃道宗宗主,自是希望道宗日趋辉煌。”蓝倾城道。
石敢当道:“可惜老夫要让你失望了。老夫并不知天玄老人的亲传弟子天残是否真的存在,自然更不可能知道他的下落。就算知晓,老夫也决不可能告诉你。”
蓝倾城的笑意一点一点地消失,脸色慢慢地沉了下来,久久不语。
半晌,他才打破沉默道:“本宗主既然可以知晓你的秘密,就同样会有办法让你说出一切。一个没有丝毫内力修为的糟老头,就是迟上几年找到他,对本宗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在这间密室中待上几年,那种滋味可不好受。”
顿了顿,又道:“本宗主知道你一定暗自企盼道宗会有人设法救你,但请老宗主莫忘了,连你最信任的人都会把你的秘密透露出去,那么你身处密室中时,与你接近的人当中,你又怎能正确判断出谁是值得你信任的人?老宗主,但愿多加小心,别再一次被你信任的人出卖。”
言罢,他似乎不想给石敢当以任何驳斥的时间,立即对伏降挥了挥手,两人先后退出密室,随即石门缓缓合上,密室内重新陷于一片昏暗。
密室中又恢复了寂静,甚至连偶尔火花爆开的“噼啪……”轻微响声也听得清清楚楚。
石敢当的神情并无什么变化。
独处,对石敢当来说,已成了一种最为习惯的生存状态,在隐凤谷的近二十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在独处中度过,这也铸就了石敢当惊人的冷静。
但这一次,石敢当却再也不能真正地平静了。蓝倾城所说的,未必全是真话,但有一点却是对石敢当有极大震撼力的,那就是蓝倾城竟然知道他的内力修为在酉、戍之交时减半!
看来,为了对付石敢当,蓝倾城的确是预谋已久,并且是处心积虑,费尽了心思。故此,蓝倾城的所作所为,已不能再简单地视作是欲除去石敢当,以巩固他的宗主地位那么简单了。
是谁将秘密透露给蓝倾城的?
蓝倾城一心想找到天残的真正目的何在?
石敢当反反复复地思忖着这一切……
战传说、小夭、爻意三人一路北行。
终于,他们见到了交错重叠的马蹄印以及车轮压过的印痕。这些痕迹,应当是卜城人留下的,由痕迹的清晰程度来看,卜城人马应当与此地相去不太远。
三人精神为之一振,不由加快了行程。
又赶了一阵,三人进入一处山隘后,到了一葫芦状的山谷中。只见山谷较为平缓处,大片范围内出现杂草灌木被劈斩压伏过,若再细细观察,还能在草丛中见到尚在冒着热气的马粪。
小夭雀跃道:“我爹一定就在前方不远处,也许穿过这山谷就可以见到我爹了!”
战传说也同意小夭的这一判断,但他却没有小夭的兴奋,因为他比小夭想得更多。殒惊天此去禅都的原因、方式都十分的微妙,所以即使自己很快就可以见到殒惊天,也未必就能改变什么。至少殒惊天本人就是一个障碍,他并不想在抵达禅都之前被人救走。
爻意贵为火帝之女,千金之体,何尝受过此等颠簸劳累?此刻只见她香腮泛红,云鬓微乱,如玉琢的鼻翼已见汗,我见犹怜,她伸手理了理鬓发,道:“好闷热的天气。”
的确如此。
山谷中竟没有一丝风,谷中的杂草树枝全都一动不动。季已是秋后,竟还如此闷热,的确少见。先前三人急着赶路,故一直忽视了这一点,此时目标在即,才意识到。
战传说抬头望了望天空,却并未见太阳,远处天边的乌云在翻涌滚动着,似在酝酿着什么。他道:“恐怕将有一场暴雨!”举目向前方望去,只见山谷在靠近“葫芦口”的那一段,两侧绝壁耸立,狰狞森然,树木却十分稀落,若是一场暴雨引得陡壁坍塌,堵住山路,那将让战传说三人要费不少周折。
当下,战传说道:“我们继续前行,争取在暴雨来临之前穿过山谷。”
小夭四下望了望,惑然道:“真会有暴雨?”空气依旧是十分的干燥。
话虽如此,但小夭还是依言策马前行,随后是爻意,最后才是战传说。
行了一阵,渐渐地接近了葫芦状山谷的“葫芦口”,小夭感到天色似乎暗下来不少,整个世界都开始显得有些不真实,因为此时本是正午。
她忍不住再度抬头向天空望去,只见先前还在天边翻涌滚动的乌云此刻竟已密布于自己正上方的天空中,黑压压的一片,以不可言喻的方式、轨迹在作着复杂莫测的变化。
以小夭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也不由为之咋舌,惊呼一声:“来得好快!”
三人下意识地加快了速度。
但暴雨降临的速度却仍是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