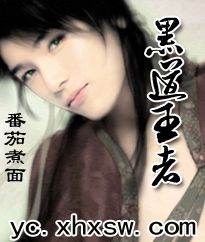正文 -- 壹。红尘一怒。
蓝可第一个真正重视的男人,叫蓝亦明。是她的亲弟弟,三岁的他或者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但他的灵魂却让蓝可忆起一生,那永远都不能摆脱的身影交缠。
蓝可记得,在五岁那年,她轻贱得比一粒尘土都不如,被所有人鄙视着。而三岁的蓝亦明,则恰恰相反,一直受宠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二十一世纪的男女观念在人们眼中依然如此强烈,谁都无法改变人的内心世界。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蓝可正在家门前河边的一棵槐树下玩。这棵树的根直插河底,枝干横卧在水面上,离水有一尺高的距离。蓝可常常一个人时坐在树上,双脚摆在水里游弋,渴望如一尾鱼般自由。拒绝眼泪与懦弱,极尽散发自己的高傲。
想事的时候,三岁的蓝亦明跑到她身后,用胖嘟嘟的上手扯着她的衣领子奶里奶气的说:姐,我要与你一起玩。扯得蓝可很烦就随手往后挥了一下,不去理会他。然后又开始想一些她想不明白的事:同是他们的孩子,为何待遇差别那么大?她不懂,五岁就会自己穿衣和鞋,会学着做饭洗碗,多么懂事的自己。却被家人唾弃着,而这一切的原由,皆因他,蓝亦明。她恨他,一如她恨自己是女孩一样的入骨贴身。虽然她弄不懂什么传宗接代,什么与亏本货的区别,可这些都不重要了,心里已被恨塞得满满的。
即使到蓝亦明死亡之即,蓝可还差点做了陪葬。那时,她心中燃烧的已不仅仅是恨。
蓝可不知道就是她挥手那轻巧的动作,让蓝亦明掉进了河里。而她当时正在想着事情,没听到他掉下去的声音。三岁的孩子,即使你拥有所有的被爱,却没有自救的能力。父母出来找时,吼声惊醒了沉思中的蓝可,她茫然无措中发现蓝亦明不见了。吼声也唤来了村子其他人。
在大家四处寻找蓝亦明时,她发现他的一只鞋正在那棵树遮住的水面上飘荡着。像一只孤独的旅者,找不到方向。她盯着那只鞋子看了好久,一直都不敢说出来。后来一位大叔的说:不会是掉进水里了吧?这几个字,不确定的疑问惊醒了所有的人,同时也把蓝可的害怕再次悬起来。
蓝可无法想象,当那句话中的不会变成会后,她,得到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她惊惧的看着面前所有的人,眼神一闪即逝。只是在看向二婶时,发现她嘴角闪过的一丝笑意。那笑,有幸灾乐祸的成份,只是蓝可弄不明白。
对这个去年嫁过来的二婶,蓝可一直不喜欢。她总觉得二婶有一种妖气,是不属于人类的。后来蓝可才明白这种感觉是什么,只是那时一切都不重要了。
是的,蓝亦明死了,死时才三岁。不懂得恨的他,把蓝可永远也得不得的爱,全部带走。
那是蓝可第一次面对死亡,一个刚刚还用小手扯她衣服的人,在瞬间就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她没有害怕。只是惊惧,惊惧下一步她自己的命运。然,母亲用双手掐着她的脖子,歇斯底里的吼着: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你这个小贱货,你赔我儿子,你赔……蓝可已难受得说不出一个字,感觉已快窒息了,却并未挣扎。后来母亲为什么放手,她已不记得,只记得那吼声骂声,和那只飘在水面上的鞋。以至以后,只要一闭上眼睛这一切就会浮现出来,面目狰狞。
第二天给蓝亦明办的丧事。家时进进出出挤满了人。年老的脸上挂着些许哀伤,而年轻一辈大多是看戏的眼神。
蓝可在房里扯了扯身上的一袭白衣。粗糙的布料,以及不健康的白,都让蓝可感觉很讨厌。她喜欢红色,喜欢像血一样让人触目惊心的红。看了看脚上早已破烂的布鞋,蓝可猛的跑到床下面,从里面抱出一个盒子。盒里面装的是一双红色绣花鞋,是今年生日时外婆送的。上面绣了大朵盛开的莲花,因为很喜欢,所以一直舍不得穿。
记得去年去外婆家时看到过,粉色的,红色的,大朵大朵妖娆的怒放着。让蓝可好生喜爱。其实四岁的她并不懂得欣赏花,只是单纯的对漂亮的事物的喜欢。
而此时,面对家里浓重的死亡气息,蓝可瘦小的神经有些承受不了。她急需要什么来缓和一下自己的身心,于是换上了这双绣花鞋。
一切弄好后,蓝可悄悄从房里出来。她看到母亲趴在蓝亦明的身上又是扯又是抓的,哭得嗓子都哑了,让人好生同情。蓝可看到这时不禁笑了起来。是的,她笑了,突然觉得心里又平衡了一些。
可能是感受到蓝可的笑。蓝母突然抬头看向他,眼晴里有藏不住的深深的恨意。啊了一声,就疯了一般朝蓝可扑去。蓝可后退再后退,力气上的悬殊让她一下子就被压倒在地上。而刚换好的那双鞋子和身上的白色孝衣,都被蓝母扯了下来,一把丢到正在燃烧的纸堆里。
火燃烧得很迅速,很疯狂。随着蓝色烟雾不停的闪烁,一切都化作一堆尘埃,灰飞烟灭。蓝可一直看着受着,脸上没有悲伤,不哭也不闹。她只是更用力的记住,蓝亦明,男人。这些坚硬的字眼。
蓝可曾一度的鄙视她的母亲,那个只知道对自己女儿撒泼对男人无能为力的女人。她没有忘记每当父亲在外醉酒回来时,找不到她便会找母亲发泄,拳脚相向咒骂不断。母亲倔强的一言不发,任他打之骂之,等他发泄完后还是把他扶回房,扔在床上。她躲在房门的后面看着这些,心里有丝丝快感。
年幼的蓝可以为此生只要看到这些吵闹与打骂,日子就会过得很快。可她忽略了,在这些残酷的场景背后,亦有她的悲惨。成长过程中所有的得与失,都是要付出相等的代价。没有人可以例外。
蓝可从不轻易描绘命运,她相信宿命,信仰幻想。
她常常在幻想中,把人生的剧本一遍一遍的修改,达到她想要的微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