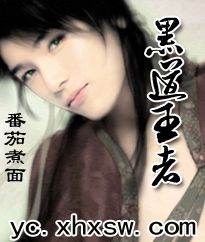正文 -- 第二十七章
“到今天我十分佩服驴客精神了,那种比狗更强的忍耐力,知道狗是遇肉吃肉,遇那什么就吃那什么了,而且跟刺猬冬眠消耗一样低。所以我说没钱就别到处跑在家呆着多好。”
我喋喋不休地跟赛可嚼着话,她显得很气馁,我晶晶姐说过绿皮火车是所有自助游旅客最大的噩梦,他们宁愿花三倍以上的钱去坐奢侈的航空工具。
第二天凌晨,队伍坐车到广州,一部分人回各自的单位,分道扬镳,巴金他们进京汇报情况,赛可北上回家看她的父母。我们下午坐火车,和火车站的人商量电视机托运的事情,虽然昨天晚上我们围着彩色电视机看得很开心,但还是觉得电视机太累赘,火车的工作人员只把电视机当普通货物放在行李厢,我虽然有些钱,但也没勇气把五百块钱不当回事情,费点口舌说电视机是易碎品,还拿了点钱出来,他们没有理会。巴金亲自说了说,铁路工作人员礼貌地讲照章办事。
我有些恼了,说:“我爸爸就是武汉铁路局的,不能通融吗?”
他们问:“你爸爸是谁?”
电视机被搬到乘务员车厢,我千恩万谢了。怪不得有人眼红铁路的铁饭碗,一句“我是铁路职工家属”,票都可以不买,我爷爷真强大。
傍晚没别的火车了,只一辆绿皮,大家说说笑笑地走上绿皮火车,刚上车,有座位我感觉还可以,只是人多了点,稍稍有点味道,到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睡着睡着不对劲了,在香港气温全年二十度左右,我们穿地是衬衫,这还没出广东省呢,怎么越来越冷,冷得睡不着,气温大概几度的模样,赶紧把身上的毛毯往巴金、艾青身上缠,赛可身上都有三条毯子,真有点早知如此不该当初了,早该知道这不是暖气车厢,没把衣服给吕蒙多好。
望着其他人冻得牙齿打颤,我开玩笑:“都别睡着了,小心别睡过去。”
话说出口就后悔了,这话把自己都给吓到了,拿出所有的衣服盖在身上,和他们挤在一起一边取暖一边不停地和赛可说着话。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逢凶化吉满天飞》,男主角罗嗦地让机长自了杀,更甚与唐僧。现在地情况有点相似,我讲了一夜的废话,赛可就这么听了一夜。
她说:“感觉你明天就要死了,把一生的话一晚上倒干净了,所以我没到明天也死了。”
我这次笑得很歉意。
第二天,艾青老先生幸灾乐祸地问我们昨天睡得好不好,早上起来我浑身象散了架,全身酸疼,尿意突然象早潮般上涨,跟他们号召上厕所,没有列宁的感染,希特勒的吼叫,众人哄应,赛可也羞答答地举起手。站起身才发现火车过道坐着站着的人坚实地象混凝土墙,我们一点点往厕所挪,用地是钻。
赛可第一个进厕所,红着脸出来。男同志们简单,四五个人围着蹲点,比赛瞄洞口,精确的如飞毛腿,有所不雅,却十分有趣。
下午,在“自然空调”车厢里,温度陡然上升,身旁到底不是混凝土,是人————人是需要动的,缓缓地蠕动,口臭、汗臭、体臭、脚臭、尿臭、屎臭从缝隙里散发出来,孟子没有坐过火车,说地话不能以面盖点,那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万紫千红的混合型臭味,积在车厢十几个小时,随空气发酵,象云层一般如实质地流动。到武汉,我们抵受不住下了火车,打算坐车走,之前,直奔澡堂,我使劲地拿臭肥皂搓了身体,那股味道好象粘在鼻子底下,洗都洗不掉,我问团里人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自欺欺人地说是幻觉,一定是幻觉。一个月后,幻觉才消失。
武汉火车站,我把电视机从火车上搬下来,今天我爷爷没上班。我陪巴老他们在附近的小餐馆撮一顿,吃厌了窝窝头,艾青老先生说他没想到自己还能吃不惯窝窝头。侧面地表现了度日如年的可行性,下午巴老他们坐客运汽车启程。我拖着电视机,大客车不敢上,拦了辆往汉口方向的驴车,把电视机丢车上,给拉车大伯十块钱,咯噔咯噔地往家的方向去。
*****************
傍晚,胡汉三又回来了,离开近一个月,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张开双臂迎接大家。
“哇,是电视机啊。”有人叫。
家里人和老邻居拢过来,对着电视机指指点点。
我尴尬地放下手,我爷爷拿过我手上的行李,问:“累不累。”
我说累,他笑了,把手掌放在我背上,拍了拍,我们一起走进屋,他给我做了一碗红烧肉盖浇饭,真香,怪不得毛主席他爱吃,估计这时的厨师都会这道拿手菜,跟《天龙八部》太祖长拳般普及。
我奶奶把电视机搬到门口,老邻居聚在院子里。晚上六点到十点,中央电视台只有四个小时的播出时间,除了新闻,只剩下样板戏,老邻居在现场和影院看过千遍的东西,但从没在电视机里观赏过。
我端着碗边吃饭边和大毛、志伟、小歪和我爸我叔聊天,两个月了,火锅店的生意很好,分给万松园居委会千元,我们自己还有千元,一直会好下去,不过市内已经有人效仿开了一家,地点在江汉路。
这个消息使我很意外,原以为半年内不会出现对手,问大毛他们:“你们去看了情况没有。”
他们都摇摇头,竞争意识还不高。改天自己去看看,只是看看而已,餐饮业是块空白,我一家也吃不完。
我爸问我香港好不好玩。
“很好,主要赚了点,是这个数。”我伸出两根手指。
“两百?”大毛猜,他至少没猜二十,有长进了。
我晃晃手指
“两千?”他再猜。
我又晃晃手指。
“啊!”大毛跳起来,手舞足蹈,绕院子一周,坐下伸出两根手指:“两万!你怎么办到的。钱你带回来了?”
一直带在身上,天下无贼了。
我轻描淡写地提了提剧本的事情,跟他们说:“香港是个发达地区,这只是九牛一毛。”
着重提另一件事情。
“在香港的见闻就那么多吧,但在大陆沿海我看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大陆沿海每天几十几百的人往香港跑,或越境,或偷渡,或签证,。逢年过节,几千人等在边境口,准备冲关,根本拦不住。
“这是怎么回事。“志伟问。
“穷呗。”我说,“香港发展很快,正需要大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一边是两千港币一个月,一边是十几块粮票,你选哪边?”
“里通外国的混蛋,一群不要脸的叛徒,为钱就愿意给资本主义剥削了!老子看到了一定把他们全枪毙。”大毛骂。
我笑着让大毛少安毋躁:“一个大陆公民在香港,就能养活大陆几十口人,是变相的赚取外汇吧,香港人好歹是自己人,总会回家,大陆公民给他们做建设不亏————好过《望乡》的南洋姐,死了都不能面朝故乡。大毛同志,你要明白这根本不是变不变节的事情,贫富差距而已,赶上去就行了,建设祖国靠谁————”
我左手抓着大毛的手,右手抓着志伟的手,抓得很紧:“是我们。”
他们点点头,说:“有一天,中国富了,美国人也来给我们打工。”
我自己也明白了,如果中国比日本强很多,就不用整天听它唧唧歪歪了,一拳就能解决问题。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该是努力的时候了,志伟、小歪我决定过几天派你们到香港出差。”